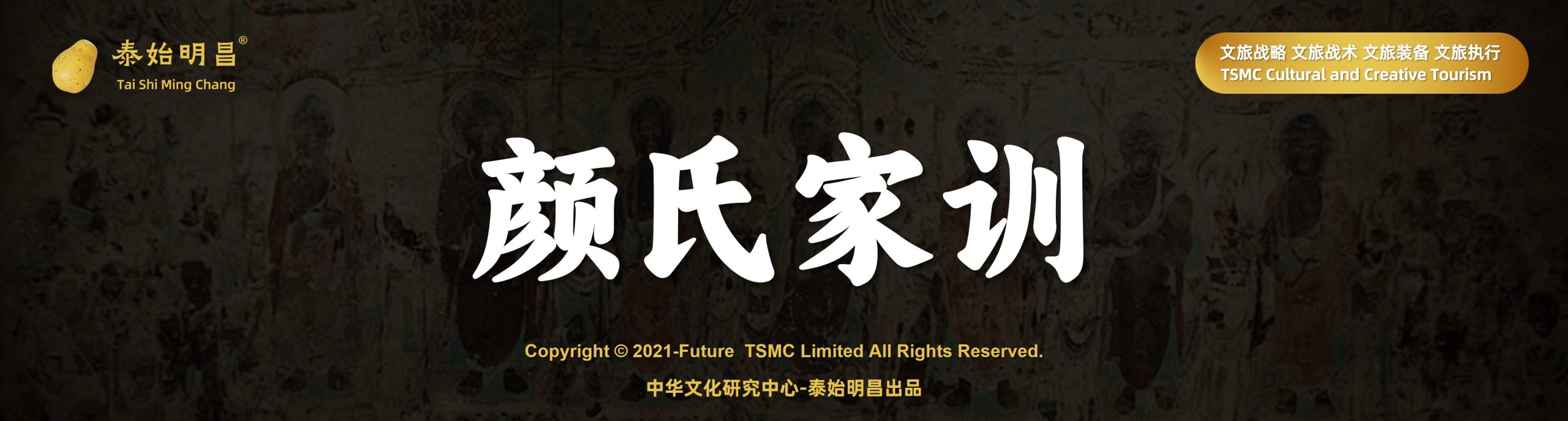作者: 颜之推(531年—约591年),北齐至隋朝文学家、教育家,历经南北朝动荡,晚年撰写《颜氏家训》以教育子孙。
年代:成书于隋朝初年(6世纪末)。
内容简要:《颜氏家训》共20篇,内容涵盖家庭教育、修身养性、处世之道等方面。颜之推结合自身经历,强调读书明理、勤俭持家、注重礼仪,并批判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它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代表作,对后世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颜氏家训-书证篇-原文
太公《六韬》,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
《论语》曰:“卫灵公问陈於孔子。”
《左传》:“为鱼丽之陈。”
俗本多作“阜”旁车乘之“车”。
案诸陈队,并作陈、郑之“陈”。
夫行陈之义,取於陈列耳,此“六书”为假借也。
《苍》、《雅》及近世字书,皆无别字,唯王羲之《小学章》独“阜”旁作“车”。
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
“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
河北经传,悉略此字。
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
至如“伯也执殳”,“於旅也语”,“回也屡空”心,“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我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
《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
按古者斜领下连於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衿,交领也。”
邺下《诗》本既无“也”字,群儒固谬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
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
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
《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太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寐。
夫虎豹穴居,事之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宁当论其六七耶?
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
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
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
答曰:“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
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
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邓?
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
且馀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
又相如《封禅书》曰:‘导一茎六穗于扈,牺双解共抵之兽,此导训择,光武诏云:‘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是也。
而《说文》云:‘道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无妨自当有禾名道,非相如所用也。
‘禾一茎六穗于扈,’岂成文乎?
纵使相如天才鄙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角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
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颜氏家训-书证篇-译文
太公的《六韬》中,有天阵、地阵、人阵、云鸟之阵。
《论语》中说:“卫灵公向孔子询问阵法的布置。”
《左传》中记载:“布置鱼丽之阵。”
俗本中多将“阵”字写作“阜”旁加“车”字。
考察各种阵队,都写作陈、郑的“陈”字。
行阵的意义,取自于陈列的意思,这是“六书”中的假借用法。
《苍颉》、《尔雅》以及近世的字书,都没有别的写法,只有王羲之的《小学章》中独独将“阜”旁写作“车”字。
即使这种写法在俗间流行,也不应该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中的原文。
“也”字是用于句末或助句的虚词,文籍中常见。
河北的经传中,都省略了这个字。
但有些地方的字是不可省略的。
比如“伯也执殳”,“於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以及《诗传》中说的“不戢,我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之类,如果删去这些“也”字,文章就会显得残缺不全。
《诗经》中说:“青青子衿”,《传》解释说:“青衿,青领也,是学子的服装。”
根据古代的记载,斜领下连着衿,所以称领为衿,孙炎、郭璞在注释《尔雅》时,曹大家在注释《列女传》时,都说:“衿,是交领的意思。”
邺下的《诗》本中没有“也”字,群儒们错误地解释说:“青衿、青领,是衣服的两个部分,都用青色装饰。”
用这种解释来理解“青青”二字,错误很大。
还有一些俗学,听说经、传中有时需要“也”字,就随意加上去,结果常常不得要领,反而显得可笑。
《后汉书》中记载:“酷吏樊晔担任天水太守时,凉州人为此作歌说:‘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的书本中“穴”字都误作“六”,学士们因循守旧,迷而不悟。
虎豹居住在洞穴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以班超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难道还要讨论是六还是七吗?
有客人质问主人说:“现在的经典,你都认为不对,《说文》中所说的,你都认为对,那么许慎比孔子还厉害吗?”
主人拍手大笑,回答说:“现在的经典,都是孔子的手迹吗?”
客人说:“现在的《说文》,都是许慎的手迹吗?”
主人回答说:“许慎根据六书的原则,按部分类,使文字不会出错,错了也能发现。
孔子保留了文字的意义而不讨论文字的形式。
先儒们尚且可以根据意义修改文字,何况是书写流传的文字呢?
比如《左传》中“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然不能随意改动,怎么敢用《说文》来校对其是非呢?
而且我也不完全以《说文》为准,如果其中引用的经传与现在的说法不符,我也不敢盲从。
又如司马相如的《封禅书》中说:‘导一茎六穗于扈,牺双解共抵之兽’,这里的‘导’字解释为‘择’,光武帝的诏书中也说:‘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这是正确的。
而《说文》中说:‘道是禾名。’并引用《封禅书》为证;这并不妨碍‘道’字本身有禾名的意思,但并不是司马相如所用的意思。
‘禾一茎六穗于扈’,这怎么能成文呢?
即使司马相如的天才鄙陋拙劣,勉强写出这样的话,那么下句也应该说‘麟双角共抵之兽’,而不应该说‘牺’字。
我曾经嘲笑许慎是个纯粹的儒者,不懂得文章的体例,像这样的例子,不足以凭信,但大体上我佩服他的书,因为它有条例,剖析了文字的根源,郑玄在注释书时,常常引用它作为证据;如果不相信他的说法,那么就会陷入迷茫,不知道一点一画的意义何在。”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颜氏家训-书证篇-注解
六韬:古代兵书,传为姜太公所著,包含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等战术。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左传:古代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著,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
鱼丽之陈:古代战术之一,见于《左传》。
六书:古代汉字的六种构造方式,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苍:《苍颉篇》,古代字书。
雅:《尔雅》,古代解释词语的著作。
王羲之:东晋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
小学章: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伯也执殳:出自《诗经》,意为伯拿着殳(一种兵器)。
於旅也语:出自《论语》,意为在旅途中说话。
回也屡空:出自《论语》,意为颜回经常贫困。
风,风也,教也:出自《诗经》,意为风既是自然现象,也是教化。
青青子衿:出自《诗经》,意为学子穿着青色的衣领。
青衿:学子的服饰,青色衣领。
孙炎:东汉学者,曾注《尔雅》。
郭璞:东晋学者,曾注《尔雅》。
曹大家:东汉学者曹大家,曾注《列女传》。
樊晔:东汉酷吏,曾任天水太守。
班超:东汉名将,曾出使西域。
许慎:东汉学者,著有《说文解字》。
说文:《说文解字》,许慎所著的汉字字典。
郑玄:东汉学者,曾注《诗经》等经典。
相如: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
封禅书:司马相如的作品,记载了封禅仪式。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颜氏家训-书证篇-评注
本文通过对古代经典文献中“陈”字的考证,揭示了汉字演变中的假借现象。作者指出,虽然俗本中将“陈”误作“车”,但根据《六韬》、《论语》、《左传》等经典文献的记载,“陈”字应作“陈列”解,而非“车乘”之意。这一考证不仅纠正了俗本的错误,还体现了古代学者对文字学的严谨态度。
文中还讨论了“也”字在经典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作者指出,虽然河北经传中常省略“也”字,但在某些语境中,“也”字不可或缺。例如,“伯也执殳”、“於旅也语”等句子中的“也”字,若省略则会影响文意的完整表达。这一讨论反映了古代学者对语言细节的重视,以及对经典文献的尊重。
此外,本文还通过对《后汉书》中“穴”字误作“六”的批评,揭示了古代文献传抄中的错误现象。作者指出,虎豹穴居是常识,不应将“穴”误作“六”。这一批评不仅纠正了文献中的错误,还体现了古代学者对文献真实性的追求。
最后,本文通过对《说文解字》的讨论,展现了古代学者对文字学的深刻理解。作者指出,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重要的字书,但其解释并非绝对正确,学者在引用时应结合其他经典文献进行考证。这一观点体现了古代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以及对经典文献的尊重。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古代经典文献中“陈”字、“也”字、“穴”字等的考证,展现了古代学者对文字学、文献学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经典文献的尊重。这些考证不仅纠正了俗本的错误,还为后人研究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