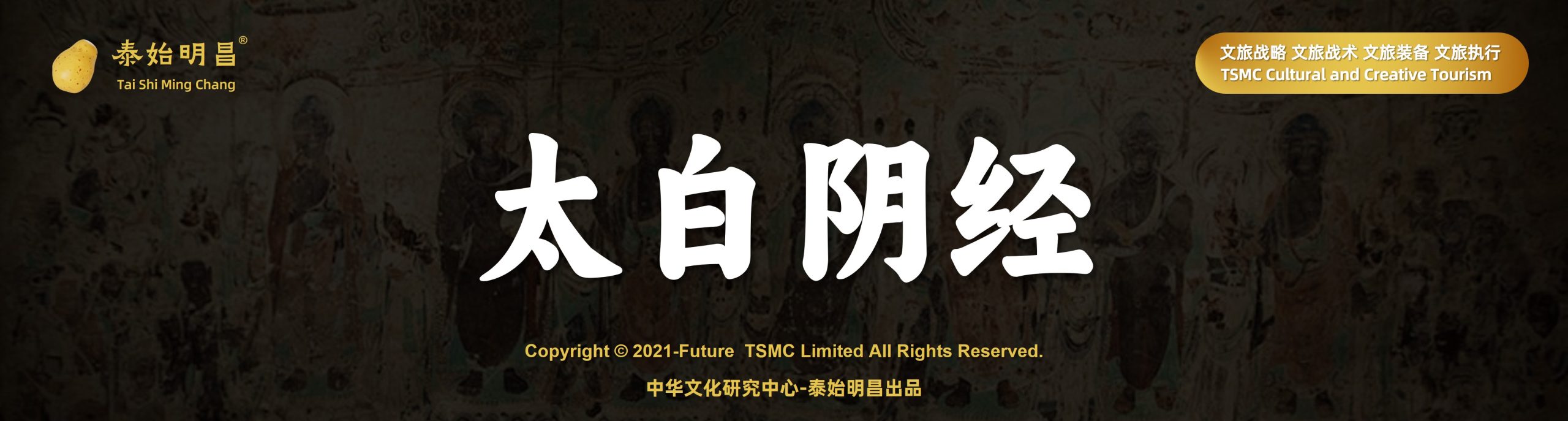作者: 李白(701年-762年),唐代著名诗人,以豪放、奔放的个性和诗才闻名。李白的诗歌以描写自然景色、人生哲理及社会风云著称,深受后人喜爱。《太白阴经》则是李白对于道家修炼和阴阳学说的总结性作品。
年代:成书于唐代(约8世纪)。
内容简要:《太白阴经》是李白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哲学与修炼作品,书中结合道家修行理论,探讨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长生不老等道家学说。李白通过这本书讲述了道家对于宇宙与人生命运的理解,并提倡修炼以求长生。在书中,他以丰富的诗词和道理展示了自己对人生、宇宙和自然的理解,并提出了理想的生活方式,书中含有大量对道家哲学的引述与思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白阴经-人谋上-贤有遇时篇-原文
经曰:贤人之生於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
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
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於地,先流其湿;
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
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於鼎饪之间,升陑而放桀。
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於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
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於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
范蠡生於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
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相与归於地户。
管夷吾束缚於鲁,齐桓任之以相。
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以政。
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
故曰:「明君之心,如明监,如澄泉。」
圆明於中,形物於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
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
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聒,聋夫以韶濩玄黄,宫徵无贯於心,
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
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
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白阴经-人谋上-贤有遇时篇-译文
经文说:贤人出生在世上,没有依靠的土地,没有显赫的宗族,没有奇特的外貌,没有智慧与勇气;他们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愚人,时而沉醉时而清醒,不能通过他们的经历或外貌来寻找,也不能通过他们的人格来识别。能够得到贤人的,在于明君的心中,道义相合而志向相同,信任的标志与言语相合,就像倒水在地上,先流向湿润的地方;就像点燃野火,先烧向干燥的地方。
所以伊尹这个莘地的农夫、夏癸这个酒店伙计,汤在烹饪的时候得到了他,提拔他并废黜了桀。太公在朝歌敲鼓、在棘津卖酒,周文王在钓鱼的时候得到了他,杀死了纣王并立了武庚。伍员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在吴国乞讨食物,阖闾被他的高尚品质所吸引,走下台阶迎接他,三天交谈后,不再有疑虑。
范蠡出生在五户人家的废墟,小时候,他内向得像盲人一样、反向得像聋子一样,当时的人认为他非常疯狂;大夫文种来看他后,知道他是个贤人,敲门拜访,一起回到了地户。
管夷吾在鲁国被囚禁,齐桓公任用他做相国。百里奚在虞国卖身,秦穆公任用他处理政务。韩信是南郑的逃兵,淮阴的胆小鬼,汉高祖刘邦用计谋收服了他。
所以说:明君的心,就像明亮的镜子,就像清澈的泉水。内心明亮,外表就能显现事物的本质,这样就能让贤人各尽其能,不浪费时机。
如果不是心有所见,不是智慧所知,只是依赖别人的看法,借别人的耳朵来听,就像用五彩斑斓的丝织品去迷惑昏花的老头,用美妙的音乐去迷惑聋子,宫商角徵的音律不能深入人心,想要找到贤人,却侥幸地希望他们自己出现,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五帝因为掌握了道而兴盛,三王因为失去了道而衰败。衰败与兴盛的道理,在于君主的心思、对贤人的使用,不在于兵力强大、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国家富裕。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白阴经-人谋上-贤有遇时篇-注解
贤人: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理想人格。
籍地:籍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或祖籍。
贵宗:贵族的宗族,指出身于显赫家族的人。
奇状:指外貌或行为与众不同。
智勇:智慧和勇气,是古代对英雄豪杰的形容。
事迹:指一个人的事迹或成就。
人物:指人,特指有特殊才能或成就的人。
明君:指英明的君主,具有仁德和智慧。
道合:道路或理念相合,指思想或行为与某种理念相一致。
志同:志向相同,指有共同的目标或理想。
信符:信物,指作为信任的凭证。
言顺:言语顺畅,指言辞得体,符合礼仪。
覆水於地:比喻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挽回。
燎火於原:比喻事情一旦开始,就会迅速蔓延。
伊尹:商汤的贤臣,以贤能著称。
莘:伊尹的故乡。
鼎饪:烹饪,指烹饪食物。
升陑:上升,指地位上升。
放桀:放逐夏桀,指推翻暴君。
太公:姜太公,周文王的贤臣。
朝歌:商朝的都城,指太公的故乡。
棘津:地名,指太公卖浆的地方。
垂纶:垂钓,指钓鱼。
武庚: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儿子,周朝建立后,武庚被立为商的后代君主。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太白阴经-人谋上-贤有遇时篇-评注
经曰:贤人之生於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
此句开篇即点明了贤人特质的不凡之处。‘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四字,强调了贤人并不因出身、地位、外貌或能力而显现其特质,而是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内在品质。‘或贤或愚’、‘乍醉乍醒’则描绘了贤人看似普通,实则深藏不露的形象。‘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进一步强调了贤人的不可测性和难以捉摸的特性。
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於地,先流其湿;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
此句进一步阐述了贤人被明君发现的原因。‘道合而志同’表明贤人与明君在理念和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默契是贤人被发掘的关键。‘信符而言顺’则形容贤人言行一致,言辞得体,如同覆水于地,燎火于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其价值。
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於鼎饪之间,升陑而放桀。
此句以伊尹为例,说明贤人并不总是以显赫的身份出现。伊尹本是一介耕夫,却在鼎饪之间被汤发现,最终辅佐汤推翻桀王,展现了贤人被发掘与使用的典型事例。
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於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
此句又以太公为例,说明贤人可以在最平凡的岗位上被发掘。太公本是一鼓刀卖浆之人,却在垂钓之时被周文王发现,辅佐周灭商,建立周朝。
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於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
此句描述了伍子胥的故事,他虽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但因其高尚的品德和才华,被吴王阖闾所重用,最终辅佐吴国强盛。
范蠡生於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相与归於地户。
此句以范蠡为例,说明贤人往往在年轻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但因其独特的行为和思想,常被世人误解。范蠡在五户之墟中长大,看似盲目和聋哑,但实则大智若愚,最终被大夫种所发现,成为一代名臣。
管夷吾束缚於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
此句列举了管夷吾、百里奚、韩信等人的事例,说明贤人可以在逆境中脱颖而出,被明君发现并重用,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故曰:「明君之心,如明监,如澄泉。」圆明於中,形物於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
此句进一步阐述了明君的特质,即具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澄澈如水的智慧。明君能够洞察人心,发现贤能,适时任用,使国家得以兴旺发达。
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聒,聋夫以韶濩玄黄,宫徵无贯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
此句批评了那些缺乏洞察力和智慧,依赖他人视听的君主。他们如同聋盲之人,无法识别贤能,注定无法求得真正的人才。
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此句总结了整段古文的主旨,指出国家的兴衰并非取决于兵力、土地、人口和财富,而在于君主是否能够识别和任用贤能。五帝之所以兴盛,三王之所以衰败,皆在于是否得其道,即是否能够发现和重用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