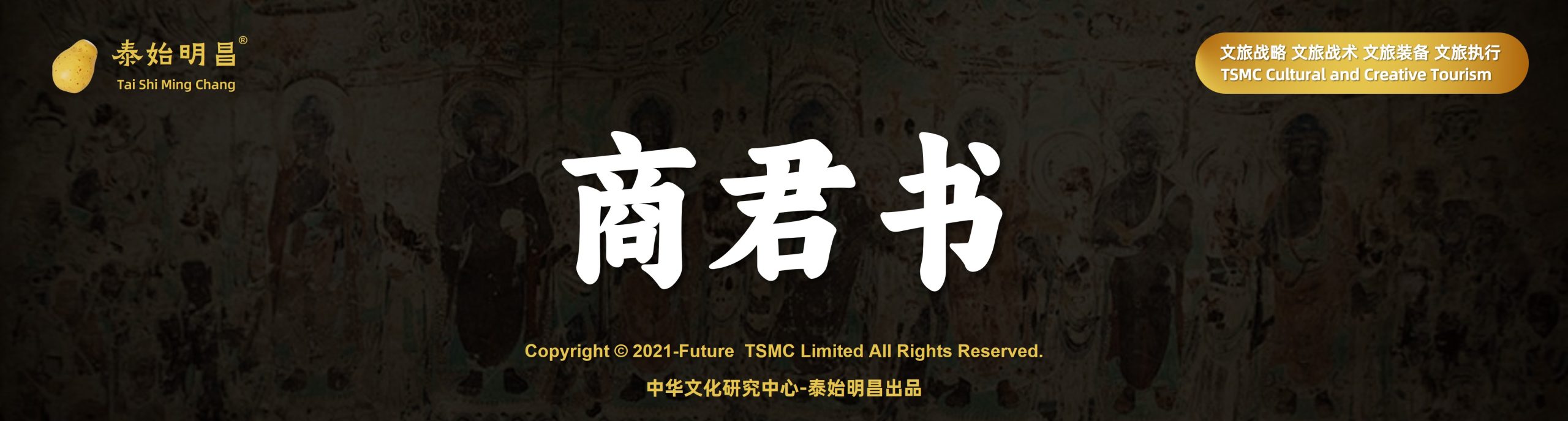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
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
民泽毕农,则国富。
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其次,为赏劝罚沮。
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十二者成朴,必削。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
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译文
如果官吏严格执行命令,那么治理就不会有遗漏;法律公平,那么官吏就不会作弊。法律一旦确定,就不能因为好言好语而损害法律。只根据功绩来任用,那么百姓就会少说闲话;只根据善行来任用,那么百姓就会多说话。如果治理偏颇,那么用五里范围来裁决的是王道,用十里范围来裁决的是强国,长期治理的就会削弱。如果用刑罚来治理,用奖赏来激励战争,只追求过错而不追求善行。所以法律一旦确立就不会改变,民众如果改变就会受到惩罚,如果计谋改变就会停止。如果重视公平与不同,那么各个都市的尊贵爵位和丰厚俸禄就会用来炫耀自己。如果国内没有奸民,那么都市也就没有奸猾的市场。如果商品过多,手工业者众多,农业松懈,奸邪之事盛行,那么国家必然会衰落。如果百姓有剩余粮食,让百姓用粮食来换取官职和爵位,官职和爵位必须根据他们的能力,那么农业就不会松懈。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必然装不满。如果授予官职、赐予爵位、发放俸禄不根据功绩,那么就失去了应有的标准。
国家贫穷却致力于战争,毒素来源于敌人,如果没有六害,国家必然强大。国家富裕却不进行战争,偷安于内,如果有六害,国家必然弱小。国家根据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这叫做用盛大的智谋来治理,用盛大的勇气来战斗。用盛大的智谋来治理,用盛大的勇气来战斗,国家必然无敌。国家根据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那么治理就会简化,言辞就会减少,这叫做用法治取代法治、用言语取代言语。如果国家根据六害来授予官职和爵位,那么治理就会变得复杂,言辞就会增多,这叫做用治理导致治理、用言语导致言语。那么君主就会专注于空谈,官员就会混乱于邪恶,邪恶的臣子就会得志,有功的人就会逐渐被排挤,这叫做失策。保持十种德行的是混乱,保持一种德行的是治理。汉朝已经安定,但喜欢使用六害的人最终会灭亡。如果百姓都致力于农业,那么国家就会富裕。如果不用六害,那么士兵和百姓都会被激励,乐于为国家效力,国内的人民都争相以此为荣,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其次,通过奖赏来鼓励,通过惩罚来阻止。再其次,百姓会厌恶它,忧虑它,羞于谈论它;装饰外表而言谈,以吃上等的食物为耻,以避免从事农业和战争;在外交上准备应对,这是国家的危机。
有饥寒死亡的情况,却不是因为利益和俸禄而战斗,这是亡国的风俗。
六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如果一个国家有这十二种现象,上面不使农民战斗,国家必然贫穷而衰落。这十二种现象聚集在一起,这就叫做君主的治理不能胜过他的臣子,官员的治理不能胜过他的百姓,这就叫做六害胜过了政治。这十二种现象如果形成群体,国家必然衰落。因此,兴起的国家不使用这十二种现象,所以国家力量强大,天下没有人能侵犯它。出兵,必然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必然能够保有;停战而不进攻,必然富裕。朝廷的官员,少的不会毁坏,多的不会损害,根据功绩来获得官职和爵位,即使有巧言令色,也不能用来互相超越,这叫做以数量来治理。用武力攻击,付出一份收获十份;用言语攻击,付出十份却损失百份。国家喜好武力,这叫做以难攻;国家喜好言语,这叫做以易攻。
重刑少赏,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为了赏赐而死亡。多赏轻刑,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不会为了赏赐而死亡。利益只从一处流出,国家必然无敌;利益从两处流出,国家只有一半的利益;利益从十处流出,国家无法守卫。重刑,明确大的制度;不明确的,就是六害。六害聚集在一起,民众就不会使用它们。因此,兴起的国家,执行惩罚时民众亲近,执行奖赏时民众获利。执行惩罚,对轻罪重罚,对重罪轻罚,那么轻罪的人不会出现,重罪的人不会到来。这叫做用刑罚去除刑罚,刑罚去除,事情就会成功;罪重而刑罚轻,刑罚到,事情就会发生,这叫做用刑罚导致刑罚,国家必然衰落。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治理民众有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掌握奖赏和惩罚来辅助仁爱,一定会得到持续。圣明的君主治理人民,必须得到他们的心,所以能够用力。力产生强,强产生威,威产生德,德产生于力。圣明的君主独自拥有这些,所以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注解
靳令:指严厉的命令或政令,强调法律的严格执行。
治不留:治理不留空隙,指治理得当,没有疏漏。
法平:法律公正,指法律不偏不倚,公平对待。
吏无奸:官员没有奸诈行为,指官员廉洁奉公。
法已定矣:法律已经确立,指法律已经制定并得到执行。
善言:好的言论,指正面的、有建设性的话语。
任功:根据功绩来任用,指根据人的功绩来授予官职。
任善:根据德行来任用,指根据人的德行来授予官职。
行治曲断:治理时要公正断案,指在治理过程中要公正地处理案件。
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在五里范围内断案可以称王,十里范围内断案可以称强,长期治理不当则会被削弱。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用刑罚来治理,用奖赏来激励战争,只追求过错而不追求善行。
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法律一旦确立就不应轻易改变,否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惩罚。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贵族和官员通过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禄位来炫耀自己。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国家没有奸邪之民,那么市场也就不会有欺诈行为。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物品繁多而民众众多,农业松弛而奸诈行为盛行,国家必定会衰落。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民众有剩余的粮食,如果让他们用粮食来换取官职和爵位,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从事农业。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必然是装不满的,比喻事情没有根基必然不能成功。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授予官职、爵位和禄位如果不根据功绩,就是没有根基的。
六虱:指六种危害国家的因素,包括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日礼乐:指过分重视礼乐,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日诗书:指过分重视诗书,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修善,曰孝弟:指过分重视修善和孝悌,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诚信,曰贞廉:指过分重视诚信和贞廉,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仁义:指过分重视仁义,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的国家治理。
曰非兵,曰羞战:指过分强调非兵和羞战,可能导致忽视国家的军事防御。
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上位者不重视农业和战争,国家必然贫穷并走向衰落。
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兴旺的国家不使用这十二种因素,因此国家强大,天下无人能侵犯。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出兵必能取得胜利,取得胜利后必能保有,停止攻击则国家必会富强。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朝廷的官员,少的不被毁坏,多的不被损害,根据功绩来取得官职和爵位,即使有巧言善辩的人也不能超越。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重刑罚而少奖赏,上位者爱护民众,民众愿意为奖赏而牺牲。多奖赏而轻刑罚,上位者不爱护民众,民众不会为奖赏而牺牲。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国家利益集中在一个地方,国家无敌;利益分散在两个地方,国家有一半的利益;利益分散在十个地方,国家无法防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重刑罚,明确大制度;不明确的是六种危害国家的因素。
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刑罚消除事情才能成功;罪重而刑罚轻,刑罚执行事情才能产生,这称为用刑罚导致刑罚,国家必然衰落。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因此治理民众有最重要的原则,因此坚持赏罚来辅助仁爱,必然能够延续下去。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圣明的君主治理人民,必须赢得他们的心,因此能够得到他们的力量。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力量产生强大,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德行,德行源于力量。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圣明的君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靳令-评注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
这两句古文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靳令,即严格的法律,能够确保治理不留空隙;法平,即法律公正,能够使官吏不敢作弊。这体现了法家思想中强调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石的观点。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这句话表明一旦法律已经确立,就不能因为言辞的美好而损害法律的权威。这反映了法家对于法律稳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视,认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不可轻易更改。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此句揭示了功与善在治理中的不同效果。任功,即根据功绩来奖赏,民众会减少抱怨;任善,即过分强调道德,民众则会多言。这反映了法家主张以功绩为标准,而非道德标准来激励民众。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这句话说明了治理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五里断者王,意味着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严格的治理,可以成为强国;十里断者强,表示在较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的治理力度,可以保持国家的强盛;宿治者削,则是指长期的治理会导致国家的削弱。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这句话体现了法家主张以刑罚和奖赏来治理国家,强调对过错的惩罚和对功绩的奖励,而不是过分追求道德。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法家认为,法律一旦确立,就应该保持稳定,不应该轻易更改。如果法律稳定,国家就会显赫;如果民众因为法律改变而受到惩罚,就会停止对法律的质疑。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
这句话说明了在法家思想中,重视等级和差别,通过给予高官厚禄来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力。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
这句话强调了法治对于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如果国家没有奸民,那么市场就不会出现欺诈行为。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
这句话指出,如果国家重视商业而忽视农业,那么国家就会衰落。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法家主张通过粮食来奖励农民,以保障农业的发展。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
这句话比喻如果国家治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就像没有底的管子,无法充满。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法家认为,授予官职、爵位和禄位应该以功绩为标准,而不是随意分配。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虽然贫穷,但致力于战争,如果没有内部的弊端,就能够强大。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相反,国家虽然富裕但不参与战争,内部腐败,有六虱存在,国家必然衰弱。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
法家主张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和爵位,认为这样能够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这句话强调了智慧和勇气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那么治理就会变得简单,言辞的争执也会减少。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如果国家根据六虱(指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来授予官职,那么治理就会变得复杂,言辞的争执也会增加。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这句话指出了国家治理中的失误,即君主过于追求言辞,官员混乱于治理,邪恶之臣得志,有功之人逐渐被边缘化。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法家主张国家应该专注于一项主要任务,而不是分散精力,这样才能实现治理。
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
这句话说明了汉朝虽然已经稳定,但那些喜欢使用六虱的人最终会失败。
民泽毕农,则国富。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能够让民众专注于农业,那么国家就会富裕。
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这句话强调了去除六虱(指不良风气)后,国家军事和民众都会积极向上,国家内部的人们都以为国家效力为荣。
其次,为赏劝罚沮。
法家主张通过奖赏和惩罚来激励和约束人们。
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
这句话说明了如果国家治理不当,民众会感到厌恶、忧虑和羞耻,从而逃避农战,导致国家危险。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法家认为,如果国家出现饥寒死亡的现象,却不是因为追求利禄而战斗,那么这就是国家的衰败之兆。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六虱指的是六种不良风气,包括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这句话指出了国家如果存在十二种不良风气,那么就会导致国家贫困和衰落。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这句话说明了如果十二种不良风气聚集在一起,那么君主和官员的治理能力就会受到挑战,六虱(不良风气)会战胜国家的政治。
十二者成朴,必削。
这句话强调了十二种不良风气如果形成,国家必然衰落。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法家认为,一个兴旺的国家不会使用十二种不良风气,因此国家力量强大,其他国家无法侵犯。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这句话说明了军事行动的成功和国家的富强。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
法家主张根据功绩来授予官职,而不是根据言辞。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这句话说明了以武力攻击比以言辞攻击更为有效。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如果喜好武力,那么在战争中就难以被攻破;如果喜好言辞,那么在战争中就容易被攻破。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
法家主张重刑轻赏,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爱护民众。
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相反,如果多赏轻刑,那么君主就不会真正爱护民众。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利益分配的重要性,利益分配得当,国家就能无敌于天下。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
法家认为,重刑和明确的法律制度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不明确的法律制度就是六虱(不良风气)的表现。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如果六虱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遵守法律。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
法家认为,一个兴旺的国家,法律执行严格,民众就会感到亲近;奖赏合理,民众就会感到利益。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这句话说明了在执行法律时,应该对轻罪重罚,对重罪轻罚,以防止轻罪者逃避惩罚。
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法家认为,通过合理的刑罚来消除刑罚,如果刑罚不当,国家就会衰落。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
这句话说明了圣明的君主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能够有效地治理民众,通过赏罚来辅助仁德。
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圣明的君主能够赢得民众的心,因此能够调动民众的力量。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这句话说明了力量、强盛、威严和德行之间的关系。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圣明的君主具有独特的才能,因此能够在天下宣扬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