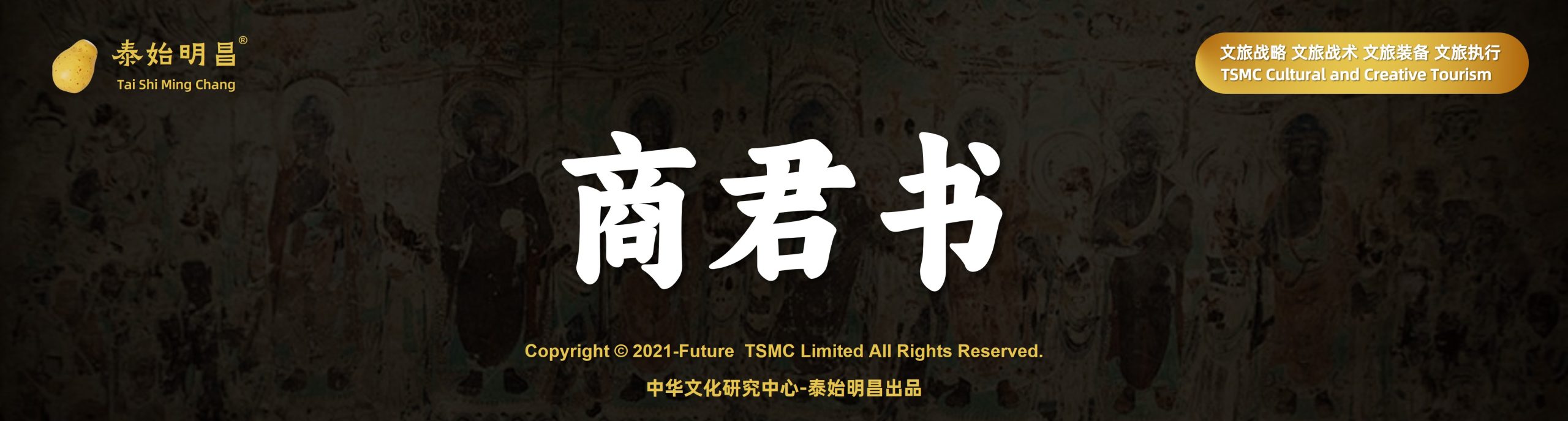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说民-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
礼乐,淫佚之徵也;
慈仁,过之母也;
任誉,奸之鼠也。
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
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
八者有群,民胜其政;
国无八者,政胜其民。
民胜其政,国弱;
政胜其民,兵强。
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
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
任奸,则民亲其制。
合而复者,善也;
别而规者,奸也。
章善,则过匿;
任奸,则罪诛。
过匿,则民胜法;
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
法胜民,兵强。
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
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
国以易攻,起十亡百。
国好力,曰以难攻;
国好言,曰以易攻。
民易为言,难为用。
国法作民之所难,
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
起一得十;
国法作民之所易,
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
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
赏轻,刑威。
爵尊,上爱民;
刑威,民死上。
故兴国行罚,则民利;
用赏,则上重。
法详,则刑繁;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
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
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
其事也乱。
故行刑,重其轻者,
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行刑。重其重者,
轻其轻者,
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
此谓治之于其乱也。
故重轻,则刑去事成,
国强;
重重而轻轻,
则刑至而事生,
国削。
民勇,
则赏之以其所欲;
民怯,
则杀之以其所恶。
故怯民使之以刑,
则勇;
勇民使之以赏,
则死。
怯民勇,
勇民死,
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
富则淫,
淫则有虱,
有虱则弱。
故贫者益之以刑,
则富;
富者损之以赏,
则贫。
治国之举,
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贫者富,
国强;
富者贫,
三官无虱。
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
力生强,
强生威,
威生德,
德生于刑。
故刑多,
则赏重;
赏少,
则刑重。
民之有欲有恶也,
欲有六淫,
恶有四难。
从六淫,
国弱;
行四难,
兵强。
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
刑于九,
则六淫止;
赏出一,
则四难行。
六淫止,
则国无奸;
四难行,
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
而利之所出一。
民非一,
则无以致欲,
故作一。
作一则力抟,
力抟则强。
强而用,
重强。
故能生力,
能杀力,
曰攻敌之国,
必强。
塞私道以穷其志,
启一门以致其欲,
使民必先行其所要,
然后致其所欲,
故力多。
力多而不用,
则志穷;
志穷,
则有私;
有私,
则有弱。
故能生力,
不能杀力,
曰自攻之国,
必削。
故曰:王者,
国不蓄力,
家不积粟。
国不蓄力,
下用也;
家不积粟,
上藏也。
国治:
断家王,
断官强,
断君弱。
重轻,
刑去。
常官,
则治。
省刑,
要保,
赏不可倍也。
有奸必告之,
则民断于心,
上令而民知所以应。
器成于家,
而行于官,
则事断于家。
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
器用断于家。
治明则同,
治暗则异。
同则行,
异则止,
行则治,
止则乱。
治则家断,
乱则君断。
治国者贵下断,
故以十里断者弱,
以五里断者强。
家断则有余,
故曰:日治者王。
官断则不足,
故曰:夜治者强。
君断则乱,
故曰:宿治者削。
故有道之国,
治不听君,
民不从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说民-译文
辩才和智慧,是混乱的助长;礼乐,是放纵淫逸的征兆;慈爱和仁慈,是过度的根源;任用和赞誉,是奸邪的庇护。混乱有了助长就能盛行,放纵淫逸有了征兆就能被采用,过度有了根源就能产生,奸邪有了庇护就不会停止。这八种情况如果聚集在一起,民众就会压倒政治;如果国家没有这八种情况,政治就能压倒民众。民众压倒政治,国家就会衰落;政治压倒民众,军队就会强大。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有这八种情况,上级就无法指挥守卫和战斗,必定会削弱直至灭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八种情况,上级就能指挥守卫和战斗,必定会兴盛直至称王。
使用善良的人,民众就会亲近自己的亲人;任用奸诈的人,民众就会亲近制度。合而为一的是善良,分别对待的是奸诈。彰显善良,过错就会隐藏;任用奸诈,罪行就会受到惩罚。过错隐藏,民众就会压倒法律;罪行受到惩罚,法律就会压倒民众。民众压倒法律,国家就会混乱;法律压倒民众,军队就会强大。所以说:用善良的民众来治理,必定会导致混乱和衰落;用奸诈的民众来治理,必定会导致治理和强大。
国家以难以攻破为强,发起攻击能以一敌十;国家以容易攻破为弱,发起攻击会以十敌百。国家喜好武力,就说它以难以攻破为强;国家喜好言辞,就说它以容易攻破为弱。民众容易受到言辞的影响,难以被使用。国家制定的法律让民众难以做到,军队使用民众容易做到的方式来攻击,就能以一敌十;国家制定的法律让民众容易做到,军队使用民众难以做到的方式来攻击,就会以十敌百。
惩罚重,爵位尊贵;奖赏轻,刑罚威严。爵位尊贵,说明上级爱护民众;刑罚威严,说明民众对上级忠诚。在兴国时实施惩罚,民众就会得到利益;使用奖赏,上级就会受到尊重。法律详细,刑罚就会繁多;法律繁多,刑罚就会减少。民众治理就会混乱,混乱之后又治理,就会再次混乱。所以在治理时,如果是在混乱中治理,就会再次混乱;如果在治理中,就会得到治理。民众的情感是混乱的,他们的行为也是混乱的。所以执行刑罚,对轻罪重罚,轻罪就不会发生,那么重罪也就无从产生,这就是在混乱中治理。如果对重罪重罚,对轻罪轻罚,轻罪就不会停止,那么重罪也就无从停止,这就是在混乱中治理。
民众勇敢,就奖赏他们所想要的;民众胆怯,就惩罚他们所厌恶的。所以用刑罚使胆怯的民众变得勇敢;用奖赏使勇敢的民众愿意去死。胆怯的民众变得勇敢,勇敢的民众愿意去死,国家没有敌手就必定称王。
民众贫穷,国家就会弱小;民众富裕,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有弊端,有弊端就会弱小。所以对贫穷的民众用刑罚,就能使他们富裕;对富裕的民众用奖赏,就能使他们贫穷。治理国家的方法,贵在让贫穷的民众富裕,让富裕的民众贫穷。贫穷的民众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民众贫穷,国家就不会有弊端。国家长期强大而没有弊端,必定会称王。
刑罚产生力量,力量产生强大,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德行,德行源于刑罚。所以刑罚多,奖赏就重;奖赏少,刑罚就重。民众有欲望和厌恶,欲望有六种放纵,厌恶有四种困难。放纵六种欲望,国家就会弱小;实行四种困难,军队就会强大。所以称王的君主,刑罚九种,奖赏一种。实行九种刑罚,六种放纵就会停止;实行一种奖赏,四种困难就会实行。六种放纵停止,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困难实行,军队就没有敌手。
民众的欲望有千万种,而利益只有一个来源。民众如果不能集中力量,就无法满足欲望,所以需要集中力量。集中力量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能强大。强大之后如果能够运用,就会更加强大。所以能够产生力量,能够消灭力量,这就是攻打敌国的强大。堵塞私路来限制他们的志向,开辟一条道路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让民众先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再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力量就会集中。力量集中而不使用,就会志向受限;志向受限,就会有私心;有私心,就会变得弱小。所以能够产生力量,但不能消灭力量,这就是自我削弱的国家。
所以称王的君主,国家不储备力量,家庭不积累粮食。国家不储备力量,是为了让民众使用;家庭不积累粮食,是为了上级收藏。
国家治理:家族决定国家,官员决定强大,君主决定弱小。重罪轻罚,刑罚就会减少。常任官员,国家就会治理。减少刑罚,保护重要事务,奖赏不可加倍。有奸邪行为的人必须报告,这样民众就会心中有数,上级下令民众就知道如何回应。器物由家庭制造,在官员那里使用,事情就在家庭中决定。所以称王的君主,刑罚和奖赏由民众心中决定,器物由家庭制造。
治理明确,民众就会一致;治理暗淡,民众就会不同。一致就会行动,不同就会停止。行动就会治理,停止就会混乱。治理时家族决定,混乱时君主决定。治理国家的人贵在让民众做决定,所以十里为单位的决定会让国家弱小,五里为单位的决定会让国家强大。家族做决定就有余力,所以说:每天都能治理的国家就能称王。官员做决定就不足,所以说:晚上才能治理的国家强大。君主做决定就会混乱,所以说:晚上才治理的国家会衰落。所以有道的国家,治理不听从君主,民众不服从官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说民-注解
辩慧:指辩论的技巧和智慧,此处指过于辩才和无知导致的社会混乱。
乱之赞也:赞,助长之意,指辩论智慧助长了混乱。
礼乐:指古代的礼仪和音乐,此处指过分追求礼乐形式而导致的放纵。
淫佚之徵也:徵,迹象,征兆,指礼乐成为放纵的迹象。
慈仁:指仁慈之心,此处指过度仁慈导致的问题。
过之母也:母,根源,指过度仁慈是各种过错的根源。
任誉:任,任用,誉,声誉,指任用那些以虚假声誉获得地位的人。
奸之鼠也:鼠,比喻微小但关键的角色,指任用这样的人会导致奸邪蔓延。
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指如果社会允许这些不良现象存在,它们就会蔓延。
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八者,指上述提到的八种不良现象;民胜其政,指民众的力量超过政府;政胜其民,指政府的力量超过民众。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善,指善良的行为;奸,指奸诈的行为;亲其亲,指民众亲近自己的亲人;亲其制,指民众亲近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力的人。
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合而复,指合乎道德的行为;别而规,指背离道德的行为。
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章,显著,明显;过,过错;匿,隐藏;诛,惩罚。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罚重,指惩罚严厉;爵尊,指爵位尊贵;赏轻,指奖赏轻微;刑威,指刑罚的威慑力。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勇,勇敢;怯,胆怯;所欲,所希望得到的;所恶,所厌恶的。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虱,比喻祸害,指国家过于富有会导致放纵,进而产生祸害。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刑,指刑罚;力,指力量;强,强大;威,威严;德,德行。
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六淫,指六种过度欲望;四难,指四种难以克服的困难。
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作一,指统一思想;力抟,指力量凝聚;强,强大。
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塞私道,指堵塞不正当的途径;启一门,指开辟正当的途径。
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刑赏,指刑罚和奖赏;器用,指工具和资源。
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指治理国家时,不应完全听从君主的命令,民众也不应完全服从官员的指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说民-评注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
此四句以比喻的手法,揭示了辩才和智慧可能导致纷争,礼乐可能导致放纵,慈仁可能导致过失,任用虚假名誉可能导致奸佞。这反映了古人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强调了过度和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
这四句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指出如果任由乱象、淫佚、过失和奸佞存在,它们就会不断滋生和蔓延,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
这里的“八者”指的是上述四种不良现象,指出如果这些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民众的力量将超过政府,导致国家衰弱;反之,如果国家中没有这些现象,政府的力量将超过民众,国家则能强盛。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
这句话强调了政治稳定和军事强大的关系,指出如果民众的力量超过了政府,国家将变得脆弱;如果政府的力量超过了民众,国家则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这是对上述观点的总结,指出如果国家存在上述不良现象,政府将无法有效地指挥守卫和战斗,国家必将衰落直至灭亡;如果国家没有这些现象,政府能够有效地指挥守卫和战斗,国家必将兴盛直至称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这句话强调了治理国家的原则,指出如果国家使用善政,民众将亲近自己的亲人;如果国家任用奸佞,民众将亲近那些奸佞的体制。
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
这里通过对比,说明了善政和奸佞的区别,善政是团结民众的,而奸佞则是分裂民众的。
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这句话指出,如果国家彰显善政,过失就会隐藏;如果国家任用奸佞,罪行就会受到惩罚。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这里说明了过失隐藏和罪行惩罚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指出如果过失隐藏,民众将胜过法律;如果罪行受到惩罚,法律将胜过民众。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这句话强调了法律和民众的关系,指出如果民众胜过法律,国家将陷入混乱;如果法律胜过民众,国家则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这是对上述观点的总结,指出如果国家以良民治理,必将导致混乱和衰落;如果国家以奸民治理,必将导致秩序和强盛。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防御能力的强弱,指出如果国家难以攻破,一次投入可以取得十倍的效果;如果国家容易攻破,一次投入可能导致十倍损失。
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
这里说明了国家防御策略的选择,指出如果国家擅长武力,则难以攻破;如果国家擅长言辞,则容易攻破。
民易为言,难为用。
这句话指出民众容易受到言语的影响,但难以被实际使用。
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这里说明了国家法律和军事策略的运用,指出如果国家法律制定得让民众难以做到,而军队使用民众容易做到的战术,一次投入可以取得十倍的效果;反之,如果国家法律制定得让民众容易做到,而军队使用民众难以做到的战术,一次投入可能导致十倍损失。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
这句话说明了惩罚和奖赏的力度,指出惩罚重,爵位尊贵;奖赏轻,刑罚威严。
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
这里说明了爵位和刑罚对民众的影响,指出爵位尊贵,上级会爱护民众;刑罚威严,民众会为上级而死。
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
这句话说明了在兴国过程中,惩罚和奖赏的作用,指出如果国家实行严厉的惩罚,民众会得到利益;如果国家使用奖赏,上级会得到重视。
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
这句话说明了法律详细程度和刑罚的关系,指出法律越详细,刑罚越繁琐;法律越繁琐,刑罚越简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这句话说明了民众治理和国家秩序的关系,指出如果民众治理导致混乱,而国家试图治理这种混乱,又会导致新的混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这句话强调了治理的时机和方法,指出如果国家在秩序良好的时候进行治理,国家将得到治理;如果国家在混乱的时候进行治理,国家将陷入新的混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
这句话说明了民众的情感和行为,指出民众的情感是稳定的,但他们的行为却是混乱的。
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这句话说明了刑罚的运用,指出如果刑罚只针对轻微的罪行,那么严重的罪行就不会发生,这就叫做在秩序良好的时候进行治理。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
这句话进一步说明了刑罚的运用,指出如果刑罚只针对严重的罪行,那么轻微的罪行就会不断发生,这就叫做在混乱的时候进行治理。
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这句话总结了刑罚的运用原则,指出如果刑罚轻重得当,国家将得到治理和强盛;如果刑罚重而轻,国家将陷入混乱和衰落。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
这句话说明了奖赏和惩罚的运用,指出如果民众勇敢,就奖赏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如果民众胆怯,就惩罚他们所厌恶的东西。
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
这里说明了奖赏和惩罚的效果,指出如果对胆怯的民众使用刑罚,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如果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他们就会愿意牺牲。
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这句话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如果能够使民众既勇敢又愿意牺牲,国家就能无敌于天下,最终称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贫富和强弱的关系,指出如果民众贫穷,国家就会弱小;如果民众富裕,国家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
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这里说明了如何通过刑罚和奖赏来调节国家的贫富,指出如果对贫穷的民众使用刑罚,他们就会变得富裕;如果对富裕的民众使用奖赏,他们就会变得贫穷。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这句话强调了治国策略,指出治国的重要策略是让贫穷的民众变得富裕,让富裕的民众变得贫穷。
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
这里说明了上述策略的效果,指出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变得强盛,官员将没有贪污。
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这句话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如果国家长期强盛且没有贪污,国家必将称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德治的关系,指出刑罚可以产生力量,力量可以产生强盛,强盛可以产生威严,威严可以产生德行,德行又源于刑罚。
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
这里说明了刑罚和奖赏的平衡,指出如果刑罚多,奖赏就会重;如果奖赏少,刑罚就会重。
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
这句话说明了民众的欲望和厌恶,指出民众的欲望有六种放纵,厌恶有四种困难。
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
这里说明了欲望和厌恶对社会和军事的影响,指出如果民众放纵欲望,国家就会变得弱小;如果民众克服困难,军队就会变得强大。
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
这句话说明了君主的治理方式,指出君主应该对九种放纵进行刑罚,只对一种困难进行奖赏。
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
这里说明了上述治理方式的效果,指出如果对九种放纵进行刑罚,六种放纵就会停止;如果只对一种困难进行奖赏,四种困难就会得到克服。
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这里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如果能够停止六种放纵,国家将没有奸佞;如果能够克服四种困难,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这句话说明了民众的欲望和利益的统一,指出民众的欲望是多样的,但利益的来源是单一的。
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
这里说明了如何统一民众的欲望,指出如果民众的欲望不统一,就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因此需要统一他们的欲望。
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
这里说明了统一欲望的效果,指出如果能够统一民众的欲望,他们的力量就会集中,国家就会变得强大。
强而用,重强。
这句话说明了力量的运用,指出如果能够有效地运用力量,国家的强大就会更加显著。
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
这里说明了力量的创造和运用,指出如果能够创造和运用力量,攻击敌国就会变得强大。
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
这句话说明了如何引导民众的力量,指出如果能够堵塞私路以限制民众的欲望,打开一条道路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使民众首先追求他们最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满足他们的欲望,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变得强大。
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
这里说明了力量和欲望的关系,指出如果力量多但得不到运用,民众的欲望就会变得枯竭;欲望枯竭,就会产生私心;有私心,国家就会变得弱小。
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
这里说明了力量创造和运用的不平衡,指出如果能够创造力量但不能运用力量,国家就会自我削弱。
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
这句话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作为君主,国家不应该积累力量,家庭不应该积累粮食。
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这里说明了上述策略的原因,指出国家不积累力量是为了让民众能够使用力量;家庭不积累粮食是为了让上级能够储备粮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
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原则,指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削弱家庭、加强官员、削弱君主。
重轻,刑去。
这里说明了刑罚的运用,指出如果刑罚轻重得当,就能够消除犯罪。
常官,则治。
这句话说明了官员的作用,指出如果官员能够常任,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
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
这里说明了刑罚和奖赏的运用,指出如果减少刑罚,重视保护,奖赏不能过多。
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
这句话说明了如何处理奸佞,指出如果发现奸佞,必须予以揭露,这样民众就会在心中做出判断,上级的命令民众就会知道如何回应。
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
这里说明了家庭和官员的作用,指出如果家庭能够制造出好的器物,而官员能够执行这些器物,那么事情就会在家庭中得到解决。
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
这里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作为君主,刑罚和奖赏的决策应该基于民众的心意,器物的制造应该基于家庭的能力。
治明则同,治暗则异。
这句话说明了治理的清晰和模糊,指出如果治理清晰,民众就会团结一致;如果治理模糊,民众就会产生分歧。
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
这里说明了治理的统一和分裂,指出如果民众团结一致,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民众产生分歧,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治则家断,乱则君断。
这里说明了治理的决策权,指出如果国家得到治理,决策权应该归于家庭;如果国家陷入混乱,决策权应该归于君主。
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
这句话说明了治理的决策层级,指出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重视下级的决策,因此以十里为单位的决策权会使国家变得弱小,以五里为单位的决策权会使国家变得强大。
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
这里说明了家庭决策的优势,指出家庭决策能够使国家有余力,因此白天治理的国家能够称王。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
这里说明了官员决策的不足,指出官员决策会使国家力量不足,因此夜晚治理的国家能够变得强大。
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
这里说明了君主决策的弊端,指出君主决策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因此长期依赖君主决策的国家会衰落。
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这句话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有道的国家治理不依赖于君主,民众不盲目服从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