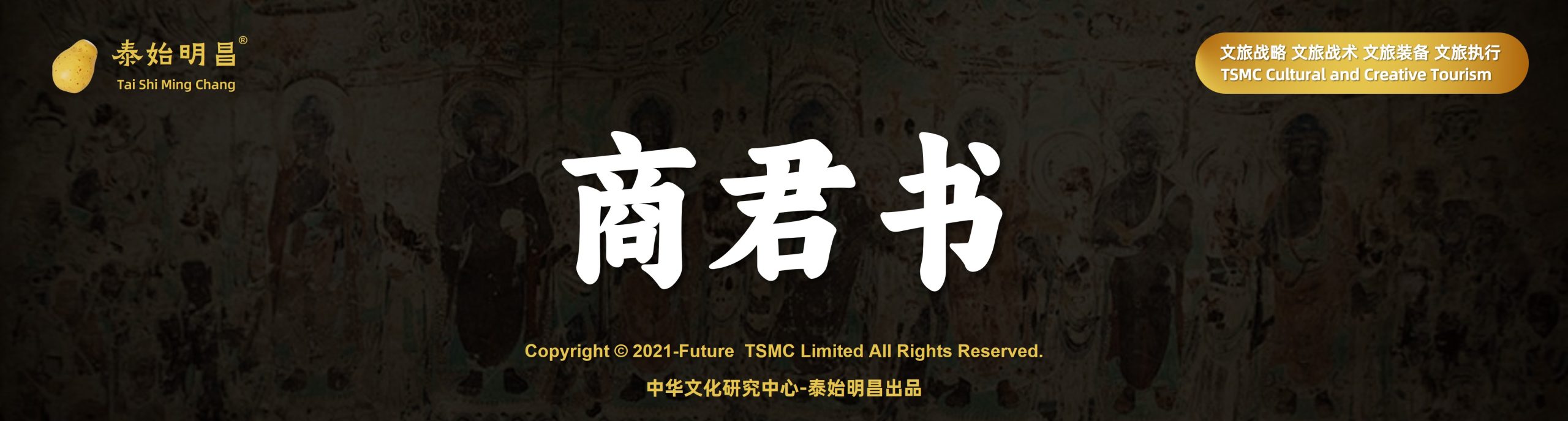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算地-原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
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
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
开,则行倍。
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
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薮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
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
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
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
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
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
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
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
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
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
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
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
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
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
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
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
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
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
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
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
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
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
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
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
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
臣请语其过。
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剽而功寡。
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
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
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
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
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
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
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
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
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
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
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
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
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
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
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
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
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
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
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
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
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
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
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
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
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
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
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
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
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
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
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
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
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算地-译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
所以有地狭而民众的地方,民众胜过土地;地广而民少的地方,土地胜过民众。
民众胜过土地,就要努力开拓;土地胜过民众,就要吸引人来。
开拓,就能行动加倍。
民众过多于土地,国家功绩就少,兵力就弱;土地过多于民众,山泽财物就无法利用。
放弃天物、纵容民众淫逸,是世主的大过错,而上下都这样做,所以民众多而兵力弱,土地大而力量小。
所以,治理国家要根据土地的情况:山林占十分之一,沼泽占十分之一,沼泽山谷流水占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十分之四,这是先王的正确法规。
所以,分配土地的数量:小亩五百,足以供一役之用,这样的土地不适宜耕种;方圆百里,能出兵卒万人的,数量太小。
这样的土地足够养活民众,城市道路足够安置民众,山林、沼泽、山谷足够提供物资,沼泽堤防足够蓄水。
所以,军队出征时,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军队休整时,民众劳作而牲畜繁衍。
这就是所谓根据土地情况来安排劳役的法规。
现在世上的君主,拥有几千里的土地,粮食不足以供应军队,而军队又要与邻国作战,我因此为世上的君主感到忧虑。
土地大而不开垦,与没有土地一样;民众多而不使用,与没有民众一样。
所以,治理国家的法则,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策略,在于统一奖赏。
私人利益被排除在外,民众就会致力于农业;致力于农业,就会朴素;朴素,就会敬畏命令。
私人奖赏被禁止,民众的力量就会集中对付敌人;集中对付敌人,就能取得胜利。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民众的本性是:饥饿了就求食物,劳累了就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求快乐,受辱了就求荣耀。
民众追求利益,就会失去礼法;追求名声,就会失去本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的盗贼,上犯君主的禁令,下失臣民的礼节,名声受辱而自身危险,却还不停止,是因为利益。
上古的贤士,衣服不暖和皮肤,食物不填满肚子,使自己意志痛苦,四肢劳累,五脏受伤,却更加富足,这不是本性的常态,而是为了名声。
所以说:名利所聚集的地方,就是民众的道路。
君主掌握名利的关键,能够取得功名的,是方法。
圣人审慎地运用权力,审慎地使用方法,方法,是臣子和君主的技术,是国家的重要。
所以,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失去方法而不危险,臣子和君主失去技术而不混乱,是从来没有的。
现在世上的君主想要开拓土地治理民众,却不审慎地使用方法,臣子想要尽力完成职责却不建立技术,所以国家有不服的民众,君主有不服从的臣子。
圣人治理国家,让民众从事农业,让他们在战争中计算。
农业是民众所苦的,战争是民众所危险的。触犯他们的苦痛,执行他们的危险,这是计算。
所以,民众活着就考虑利益,死了就考虑名声。名利所在,不可不审慎。
利益来自土地,民众就会尽力;名声来自战争,民众就会拼死。
让民众尽力,草就不会荒芜;让民众拼死,就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而草不荒芜,富强的功业就可以坐享其成。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世上的君主所关注的,都不是国家的急务。
自身有尧、舜的品德,而功绩不及汤、武的策略,这是掌握权力的人的过错。
请允许我指出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放弃势力而任由说客,就会自身孤立而功绩少。
所以,事奉《诗经》、《尚书》的说客,民众就会游荡而轻视君主;事奉隐居的贤士,民众就会远离而不尊敬君主;事奉勇士,民众就会争斗而轻视禁令;技艺之士被任用,民众就会轻率而容易迁徙;商贾之士安逸且有利可图,民众就会攀附而议论君主。
所以,这五种人加在国用上,就会导致田地荒芜而兵力弱。
说客的资本在于口才,隐居的贤士的资本在于思想,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技艺之士的资本在于手艺,商贾之士的资本在于身体。
所以,天下只有一个家,而他们的资本都在身体上。民众的资本重于身体,而他们把势力的托付偏向外部。
带着重资,归附偏私之家,这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所以汤、武禁止他们,就能建立功业而成就名声。
圣人不是能以世人容易的战胜困难的,一定要以困难的战胜容易的。
所以,民众愚昧,智慧可以战胜他们;世人聪明,力量可以战胜他们。
臣子愚昧,容易出力而难于施展智慧;世人机智,容易施展智慧而难于出力。
所以神农教人们耕作而统一天下,是因为他运用了智慧;汤、武使国家强大而征讨诸侯,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力量。
现在世人机智而民众淫逸,却效仿汤、武的时代,而做神农的事情,这是跟随世人的禁令。
所以,千乘之国混乱,这就是他们所关注的事情过于偏颇。
民众的生活:衡量而取长,称量而取重,权衡而求利。
明君慎重地观察这三者,国家就能治理好,民众就能得到。
国家之所以求民,少;民众之所以逃避求索,多。
让民众从事农业,让他们在战争中集中精力,这就是圣人的治理方法。
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境内之民就会一心;民众一心,就会从事农业;从事农业,就会朴素;朴素,就会安居而厌恶出外。
所以,圣人治理国家,让民众的资本藏于土地,而把危险托付在外。
资本藏于土地,就会朴素;托付在外,就会迷惑。
民众在内则朴素,在外则迷惑,所以他们会努力耕作而谨慎战斗。
民众耕作努力,资本就重;战斗谨慎,邻国就危险。资本重,就不会背井离乡;邻国危险,就不会归附。
在没有资本、归附危险之外的人,是疯狂的人不会做的。
所以,圣人治理国家,观察风俗来制定法律,就能治理好;观察国家根本,就能适宜。
不观察时代风俗,不观察国家根本,那么法律虽然制定,民众却会混乱,事情虽然繁忙,功绩却很少。
这就是我所说的过错。
刑罚是用来禁止邪恶的;而奖赏是用来辅助禁止的。
羞辱和劳苦是民众所厌恶的;显赫和安逸是民众所追求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刑罚不可厌恶,而爵位和禄位不足以追求,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兆。
刑罚执行不严,小人就会放纵淫逸而不怕刑罚,就会侥幸于民众和君主,利用民众和君主谋取利益。
追求显赫和荣耀的门路不止一条,君子就会追求权势来成名。
小人不遵守禁令,所以刑罚繁多。
君子不设立命令,就会实施惩罚。
刑罚繁多而惩罚实施,国家就会多奸邪,富者不能保住财富,贫者不能从事事业,田地荒芜而国家贫穷。
田地荒芜,民众就会欺诈生存;国家贫穷,君主就会缺乏赏赐。
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刑罚的人没有国家职位,被处决的人没有官职。
刑罚的人有职位,君子就会降低他们的地位;衣锦食肉,小人就会渴望他们的利益。
君子降低他们的地位,就会感到羞耻;小人渴望他们的利益,就会攻击奸邪。
所以,刑罚是用来阻止奸邪的;而官职和爵位是用来鼓励功绩的。
现在国家设立爵位而民众感到羞耻,设立刑罚而民众感到快乐,这是法律和策略的弊端。
所以,君子掌握权力,保持正直来建立策略,设立官职和爵位来匹配,论功行赏来任用,这样就能使上下称职。
上下称职,臣子就能尽其力,君主就能专其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算地-注解
世主:指古代的君主,即国家的统治者。
用兵:指发动战争。
不量力:指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而轻举妄动。
治草莱者:指负责治理荒地的官员。
不度地:指不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理。
地狭而民众:指土地面积小但人口众多的地区。
民胜其地:指人口过多导致土地资源紧张。
地广而民少:指土地面积大但人口稀少的地区。
地胜其民:指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相对较少。
务开:指努力开拓土地。
事徕:指吸引人口。
行倍:指行动效率加倍。
民过地:指人口过多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
国功寡而兵力少:指国家功绩少,兵力不足。
山泽财物:指山川湖泊中的资源。
遂民淫:指放纵民众的欲望。
世主之务过:指君主的政策失误。
地:指土地。
民:指人民。
任地:指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理。
山林居:指居住在山林。
薮泽:指湖泊。
谿谷:指山谷。
都邑蹊道:指城市和道路。
正律:指正确的法则。
分田数:指分配田地的数量。
小亩:指小片的土地。
方土百里:指方圆百里的土地。
出战卒万人:指能够出战的士兵有一万人。
垦田:指开垦土地。
食其民:指供给民众食物。
都邑遂路:指城市和道路。
供其利:指提供资源。
畜:指储存。
任地待役:指根据土地情况安排役务。
食不足以待役:指粮食不足以维持役务。
实仓:指充实仓库。
臣:指臣子,这里指作者自己。
垦草:指开垦荒地。
壹赏:指统一的奖赏制度。
私利:指个人利益。
务:指努力。
计战:指计算战争。
入令民以属农:指在国内让民众从事农业。
出令民以计战:指在国外让民众参与战争。
处士:指隐居的士人。
勇士:指勇敢的战士。
技艺之士:指有技艺的人。
商贾之士:指商人。
资:指财富。
圜身资:指全身的财富。
偏托势于外:指将财富寄托在外部势力上。
执柄:指掌握权力。
世之所易:指世人容易做到的事情。
世之所难:指世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神农:指中国远古时期的农业之神。
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
效汤、武之时:指模仿商汤和周武王的时代。
神农之事:指神农氏的事迹,这里指农业。
随世禁:指顺应时代的禁令。
千乘:指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指中等国家。
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指国内让民众从事农业,国外让民众参与战争。
计利:指考虑利益。
虑名:指考虑名声。
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指土地产生的利益让民众尽力。
名出于战,则民致死:指战争产生的名声让民众拼死。
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指国内让民众尽力,则土地不会荒芜。
出使民致死,则胜敌:指国外让民众拼死,则能战胜敌人。
加务:指过分关注。
《诗》、《书》:指《诗经》和《尚书》,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
谈说之士:指善于言辞的人。
资在于口,意,气,手,身:指财富分别来源于口才、思想、勇气、技艺和财富本身。
尧、舜之行:指尧和舜的德行。
汤、武之略:指商汤和周武王的策略。
剽:指轻浮。
说说:指空谈。
游:指游荡。
轻其君:指轻视君主。
远而非其上:指远离并否定上级。
竞而轻其禁:指争相轻视禁令。
剽而易徙:指轻浮且容易迁移。
佚且利:指安逸且有利可图。
缘而议其上:指攀附并议论上级。
五民:指五种不同类型的人。
资重于身:指财富比自身更重要。
挟重资,归偏家:指携带大量财富,投靠偏僻的家庭。
汤、武禁之:指商汤和周武王禁止这些行为。
功立而名成:指功绩建立,名声成就。
执柄之罪:指掌握权力者的罪过。
审权:指审慎地掌握权力。
审数:指审慎地计算。
数者:指计算的方法。
臣主之术:指臣子和君主的方法。
国之要:指国家的重要。
万乘失数:指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失去计算的方法。
臣主失术:指臣子和君主失去方法。
犯其所苦,行其所危:指做民众所痛苦和危险的事情。
计利,虑名:指考虑利益和名声。
利出于地,名出于战:指土地产生利益,战争产生名声。
民资藏于地,偏托危于外:指民众的财富藏在土地里,而将风险寄托在外部。
观俗立法:指观察风俗来制定法律。
察国事本:指观察国家事务的根本。
刑:指刑罚。
赏:指奖赏。
羞辱劳苦:指感到羞耻、劳累。
显荣佚乐:指显赫、荣耀、安逸、快乐。
亡国之兆:指国家灭亡的征兆。
刑人复漏:指刑罚执行不力。
小人辟淫而不苦刑:指小人放纵欲望而不惧怕刑罚。
徼倖于民、上:指在民众和上级那里侥幸逃脱。
徼于民、上以利:指在民众和上级那里谋取利益。
求显荣之门不一:指追求显赫和荣耀的途径不统一。
君子事势以成名:指君子通过权势来成名。
小人不避其禁:指小人不怕法律的禁止。
刑烦:指刑罚繁多。
罚行:指处罚执行。
国多奸:指国家有许多奸邪之人。
守其财:指保护自己的财富。
事其业:指从事自己的事业。
田荒:指田地荒芜。
国贫:指国家贫穷。
诈生:指欺诈行为产生。
上匮赏:指上级缺乏奖赏。
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指受刑的人没有国家职位,被杀的人没有官职。
衣锦食肉:指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食物。
小人冀其利:指小人希望得到利益。
羞功:指羞耻于功绩。
伐奸:指夸耀自己的奸诈。
法术之患:指法律和策略的弊端。
操权一正以立术:指掌握权力并正直地建立策略。
立官贵爵以称之:指设立官职和爵位来匹配。
论荣举功以任之:指根据荣誉和功绩来任命。
上下之称平:指上下之间的评价公平。
专其柄:指掌握权力。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算地-评注
此段古文出自《管子·权修》,作者通过对比和分析,阐述了治国之道。首先,作者指出凡世主之患在于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这导致民胜其地或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则务开,地胜其民则事徕,这反映了治国者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
作者进一步提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需要开拓土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需要吸引民众。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体现了先王治国理念的精髓。
在论述地与民的关系时,作者强调开垦土地的重要性,指出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这表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军队的强大至关重要。
接着,作者提出了‘任地待役之律’,即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来分配田地和兵力,确保国家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能有充足的资源。
在分析民性时,作者认为民之性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这揭示了人的基本需求和心理特点,对于治国者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还指出,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这表明,在追求利益和名誉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偏离正道,因此治国者需要引导民众回归正途。
在论述治国策略时,作者强调‘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这意味着治国者需要审慎地运用权力和策略,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众的幸福。
作者进一步指出,治国者需要重视农业和战争,通过发展农业来保障民众的生活,通过战争来维护国家的安全。这种内外兼顾的策略,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在分析治国者的过错时,作者批评了那些舍势任说、事处士、事勇士、技艺之士用、商贾之士佚且利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会导致国家田荒而兵弱。
最后,作者强调刑与赏的作用,指出刑者所以禁邪,赏者所以助禁。治国者需要运用刑赏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要关注民众的需求,确保国家的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