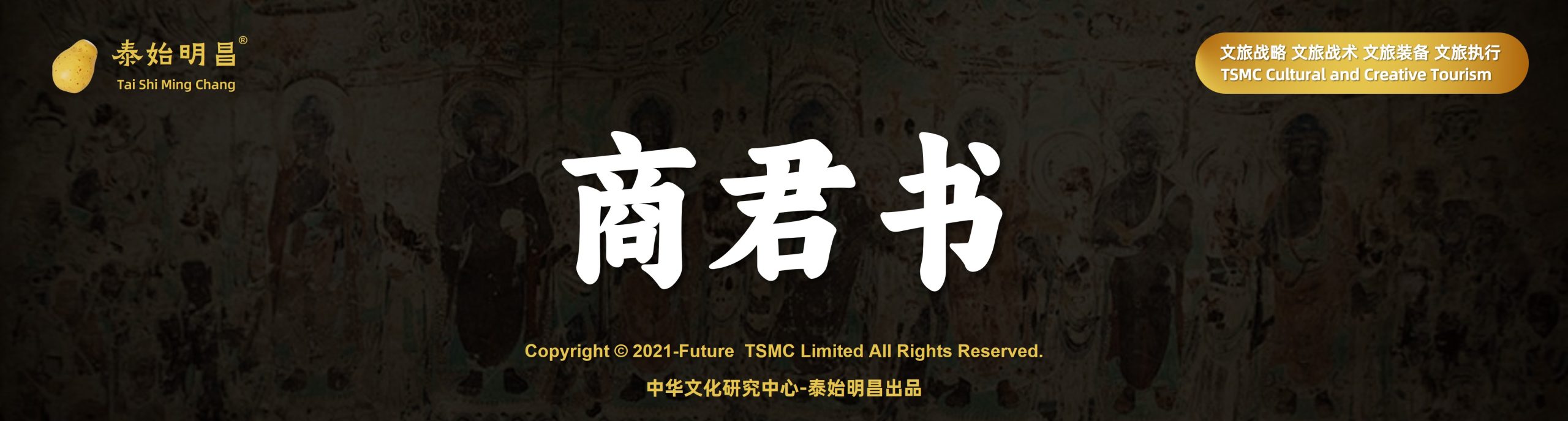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
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
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
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
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此俗之所惑也。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
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
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
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
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
国治必强。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
二国行之,兵则少寝。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
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
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译文
天地形成之后,人类开始生活。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的道德观念是以亲情为重,偏爱私情。以亲情为重就会产生分别,偏爱私情就会变得险恶。如果民众都追求分别和险恶,那么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在这个时候,人们追求胜利和武力征服。追求胜利就会产生争斗,武力征服就会导致诉讼,诉讼没有公正,就无法满足人们的本性。因此,贤明的人会立下中正之道,设定无私的原则,这样民众就会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亲情被废弃,尊重贤能的人被推崇。所有仁爱的人都以爱利为追求,而贤能的人以相互提升为原则。如果民众没有制度约束,时间久了,相互提升的原则就会导致混乱。因此,圣人继承了这些原则,制定了土地、财富、男女的分配。分配确定但没有制度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禁令;禁令设立但没有管理者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官员;官员设立但没有统一是不行的,所以设立了君主。既然设立了君主,那么尊重贤能的人被废弃,尊重贵族的人被推崇。那么在上古时期,人们尊重亲情和私情,在中古时期,人们尊重贤能和仁爱,在近古时期,人们尊重贵族和官位。尊重贤能的人以道德相互提升,而设立君主的人使贤能无用。尊重亲情的人以私情为原则,而中正的人使私情无法实行。这三者并不是相反的,而是因为民风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也随之改变。所以说:王道有规律可循。
王道是一个方面,臣道也是另一个方面,它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同,但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说:民众愚昧,就可以用智慧来统治;世界聪明,就可以用力量来统治。民众愚昧,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界聪明,智慧有余而力量不足。民众生活,不知道就学习,力量用尽就服从。因此,神农教人们耕作而统治天下,是因为他的智慧;汤、武强大而征讨诸侯,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民众愚昧,不会怀有智慧去问问题;世界聪明,没有多余的力量去服从。因此,用王道统治天下的人并重刑罚,用武力征讨诸侯的人退而重视道德。
圣人不会效法古代,也不会改变现在。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改变现在就会受到时势的限制。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朝,三代各有不同的时势,但都可以统治天下。因此,兴起王道有方法,但维持王道的方法不同。武王逆取天下而重视顺从,争夺天下而推崇谦让。他通过力量取得天下,但用正义来维持。现在强大的国家忙于兼并,弱小的国家忙于守卫,上不如虞、夏时期,下不学习汤、武时期。汤、武时期结束,所以大国有能力不战,小国有能力不守。这种道路被堵塞已经很久了,但世上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废除它,所以三代之后没有第四代。不是明智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听取这些。
古代的民众朴实而敦厚,现在的民众机巧而虚伪。因此,效法古代的人,先注重道德而治理;效法现在的人,先注重刑罚而立法。这就是俗世所迷惑的地方。现在世人所说的义,是将民众所喜欢的建立起来,而废弃他们所厌恶的;他们所说的不义,是将民众所厌恶的建立起来,而废弃他们所喜欢的。这两种情况名义上交换了实质,不能不仔细观察。建立民众所喜欢的,民众就会伤害他们所厌恶的;建立民众所厌恶的,民众就会安心于他们所喜欢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民众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超出常规;民众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逸乐。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民众就会敬畏,敬畏就不会有奸邪,没有奸邪,民众就会安心于他们所喜欢的。用道德教育民众,民众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导致混乱,混乱就会导致民众伤害他们所厌恶的。我所说的刑罚,是道德的基础;而世人所说的道德,是暴力的道路。正道民众的人,用他们所厌恶的,最终会达到他们所喜欢的;用他们所喜欢的,最终会败坏他们所厌恶的。
治理国家刑罚多而奖赏少,所以王者刑罚九次而奖赏一次,削弱的国家奖赏九次而刑罚一次。过错有轻重之分,刑罚有轻重之分;善行有大小之分,奖赏有大小之分。这两者,是世人常用的。刑罚加在罪行的最终结果上,奸邪就不会消除;奖赏给予民众认为正确的事情上,过错就不会停止。刑罚不能消除奸邪而奖赏不能停止过错,必然会导致混乱。因此,王者刑罚用于防止将要发生的过错,那么大奸邪就不会产生;奖赏给予举报奸邪的人,那么小过错就不会遗漏。治理民众能够使大奸邪不产生、小过错不遗漏,那么国家就会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就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国内就会独善其身。两个国家这样做,战争就会减少。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这就是我之所以认为杀戮刑罚与道德相反,而道德与暴力相合的原因。
古代的民众杂居在一起,因为混乱,所以寻求有君主来治理。那么,天下人喜欢有君主,是为了治理。现在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其害处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混乱,与没有法律相同。天下不安定没有君主,但喜欢胜过法律,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迷惑。对天下民众最有利的是治理,而治理最安宁的是设立君主,设立君主的方法最广泛的是胜过法律,胜过法律的要点最急切的是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根本最深刻的是严厉的刑罚。因此,王者用奖赏来禁止,用刑罚来鼓励;寻求过错而不是寻求善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
古代的民众杂居在一起,因为混乱,所以寻求有君主来治理。那么,天下人喜欢有君主,是为了治理。现在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其害处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混乱,与没有法律相同。天下不安定没有君主,但喜欢胜过法律,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迷惑。对天下民众最有利的是治理,而治理最安宁的是设立君主,设立君主的方法最广泛的是胜过法律,胜过法律的要点最急切的是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根本最深刻的是严厉的刑罚。因此,王者用奖赏来禁止,用刑罚来鼓励;寻求过错而不是寻求善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注解
天地设而民生之:天地形成之后,人类开始生活。这里的‘天地’指的是宇宙的创造和自然法则,‘民生’指的是人类的生活。
母:指母亲,这里用来比喻人们首先认识到的亲情。
父:指父亲,这里用来比喻人们后来认识到的亲情。
亲亲:亲近亲人,强调家庭和血缘关系。
爱私:爱自己的私人利益。
别:区分,分别对待。
险:危险,不稳定。
民众:民众众多。
务胜:追求胜利。
力征:依靠武力征服。
正:公正,正确。
上贤:推崇有德行的人。
仁:仁爱,道德。
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对土地、财富和性别进行划分。
禁:禁止,限制。
官:官员,政府机构。
君:君主,国家的统治者。
上世:古代,过去的时代。
中世:中期,中间的时代。
下世:后期,后来的时代。
神农:传说中的农业神,代表农业文明。
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武: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虞: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刑:刑罚,法律制裁。
赏:奖赏,奖励。
德:道德,德行。
法:法律,规章制度。
治:治理,管理。
民:人民,民众。
藂生:草木丛生,形容原始、朴素的状态。
上:上位,统治者。
奸:邪恶,不诚实的行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开塞-评注
天地设而民生之,此句开篇即点明了天地自然形成,人类生活随之产生。‘天地’在此象征着宇宙的秩序与规律,‘民生’则代表人类社会的建立与延续。这句话强调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古人对宇宙与人类关系的深刻认识。
‘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这里描述了人类社会初期的状况,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父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血缘关系和亲情观念。‘亲亲’和‘爱私’则揭示了早期社会的道德观念,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重视亲情而忽视他人。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这两句进一步阐述了‘亲亲’和‘爱私’的弊端,即过分重视亲情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疏离,而过分自私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这句话指出了民众过于追求区分和危险行为会导致社会动荡。‘民众’在此指代整个社会,‘别’和‘险’则指代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
‘务胜而力征。’这句话描述了人们追求胜利和力量的竞争心态,‘力征’则指通过武力来征服他人。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这里说明了过度竞争和武力征服会导致争斗和诉讼,而如果没有正义的裁决,人们就无法得到满足。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这句话提出了贤者应该树立中正之道,摒弃私欲,从而让民众感受到仁爱。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这句话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亲情观念逐渐被贤者之道所取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仁者和贤者的行为准则,即仁者以爱利为务,贤者以相互帮助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这句话指出了如果民众没有秩序和规则,长期下去就会导致混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这里说明了圣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了土地、财产和男女的分配规则。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这句话描述了从制定规则到设立官员,再到建立君主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这句话说明了君主制度的建立使得贤者之道被贵族地位所取代。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句话总结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这里指出了贤者之道在君主制度下失去了作用。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这句话说明了亲情观念和私欲在道德规范下被限制。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这句话指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变化。
‘故曰:王道有绳。’这句话强调了王道(即治国之道)需要有明确的原则和规范。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这句话说明了王道和臣道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这句话指出了民众的智慧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而世界的力量也可以用来统治。
‘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这里说明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治理国家时的作用。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这句话指出了通过刑罚和武力来统治国家的方法。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这句话说明了圣人不会盲目效仿古代,也不会拘泥于现代。
‘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这句话指出了盲目效仿古代或拘泥于现代都会导致落后。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这句话说明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但都可以实现国家的统治。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这句话指出了兴国之道和维持国家统治的方法是不同的。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这句话描述了武王通过武力夺取天下,但重视顺应天意,推崇谦让。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这句话说明了武王在夺取天下时依靠武力,但坚持正义。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这句话指出了当时强国的扩张和弱国的守势,以及与古代相比的不足。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这句话说明了汤、武时代的国家治理模式。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这句话指出了当时国家治理模式的僵化。
‘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希望有明主能够改变现状的愿望。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这句话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众的不同特点。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应该借鉴古代的道德和现代的法律。
‘此俗之所惑也。’这句话指出了当时社会的迷惑。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这句话指出了当时社会对‘义’和‘不义’的误解。
‘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强调了要认清‘义’和‘不义’的本质。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这句话说明了民之所乐与民之所恶之间的关系。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这句话指出了民众在忧愁和快乐时的不同表现。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可以维护社会秩序。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这句话指出了道德教育可能导致的后果。
‘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这句话指出了作者对‘刑’和‘义’的理解。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这句话说明了正民之道。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应该根据罪行的轻重和善行的多少来决定。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的作用。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这句话指出了刑罚和赏赐不能有效治理国家的后果。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这句话说明了刑罚和赏赐的正确使用。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
‘国治必强。’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
‘二国行之,兵则少寝。’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可以减少战争。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这句话说明了国家治理的成功可以恢复道德。
‘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这句话指出了杀刑与道德和暴力的关系。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这句话说明了古代社会因为混乱而需要建立君主制度。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这句话说明了人们喜欢有君主的原因。
‘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这句话指出了有君主但没有法律和有法律但无法治理的后果。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这句话说明了人们对于君主和法律的态度。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这句话说明了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