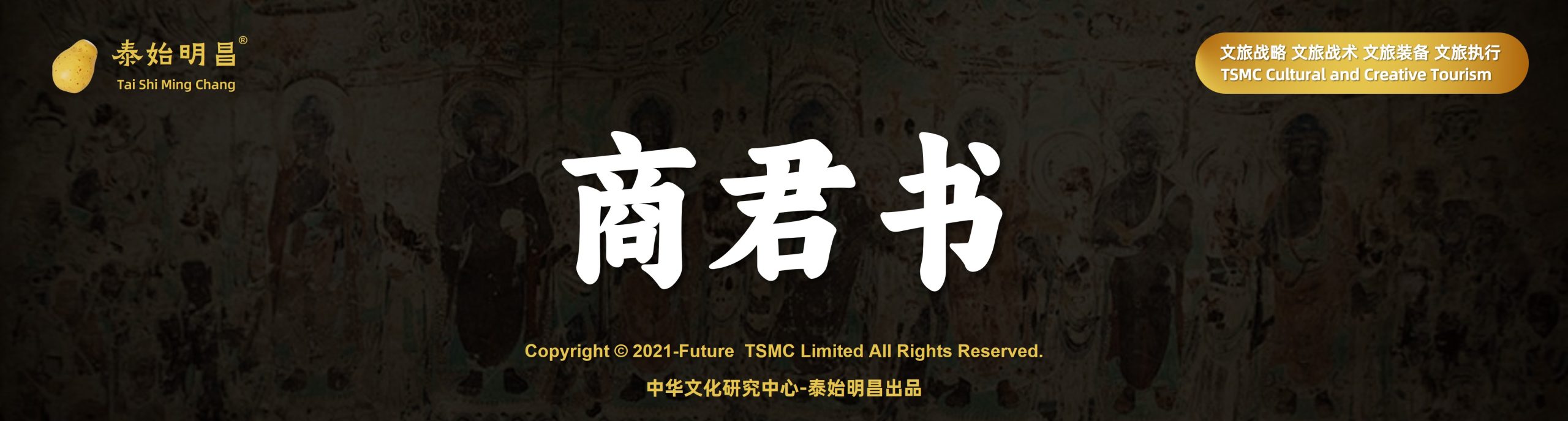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农战-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
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具备,国之危也。
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
则民朴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
不可巧取,则奸不生。
奸不生,则主不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
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
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
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
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
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
仓虚,主卑,家贫。
然则不如索官。
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
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
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 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 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 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 如此,则不远矣。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 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故先王反之于农战。 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 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 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 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 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 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 主好其辩,不求其实。 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 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 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 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 此贫国弱兵之教也。 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 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农战-译文
凡人君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如今民众追求官爵,都不以农战为手段,而是依靠巧言虚道,这就是劳民。劳民的国家,必定无力;无力者,国家必定衰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教育民众时,都让他们专注于某一件事而获得官爵,因此没有人不追求官职和爵位。
国家摒弃了空谈,民众就会变得朴素;民众朴素,就不会放纵。民众看到官爵的利从单一途径产生,就会专注于某一件事;专注于某一件事,民众就不会偷懒。民众不偷懒,国家就有力量;力量强大,国家就强大。
现在国内的人民都说:‘可以避开农战,却可以得到官爵。’因此,豪杰们都可以改变职业,学习《诗》、《书》,追随外部势力;向上可以显赫,向下可以求取官职和爵位;那些懦弱的人从事商业,学习技艺,都是为了逃避农战。
如果民众把这种教育方式当作榜样,那么国家的粮食必定减少,军队必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仓库满了,也不会放松农业;国家大了,人口多了,也不会沉溺于空谈。这样,民众就会变得朴素。
民众朴素,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就不会产生奸邪。奸邪不生,君主就不会被迷惑。
现在国内的人民和那些担任官职的人,看到朝廷可以通过巧言令色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无法保持稳定。
因此,向上时曲意逢迎君主,退下时考虑私利,为了实现私利,就出卖权力。那些曲意逢迎君主、考虑私利的人,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爵位和禄位;那些出卖权力的人,并不是忠臣,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所以那些希望升迁的下级官员都说:‘如果有很多财富,就可以得到上级的青睐。’他们说:‘我不通过财富来事奉上级而寻求升迁,就像用猫来诱捕老鼠一样,肯定不会成功;如果用感情来事奉上级而寻求升迁,就像拉着一根断了的绳子去攀爬弯曲的树木一样,更加不会成功。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采取下策,动员民众收集财富来事奉上级,以寻求升迁呢?’
百姓说:‘我们厌恶农业,先充实公仓,收集剩余的粮食来养家;为了君主忘我战斗,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仓库空虚,君主地位低下,家庭贫穷。那么不如去追求官职。’亲戚朋友聚集,就会产生新的忧虑。
豪杰们努力学习《诗》、《书》,追随外部势力;那些懦弱的人从事商业,学习技艺,都是为了逃避农战。如果民众把这种教育方式当作榜样,那么粮食怎能不减少,军队怎能不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官法明确,因此不需要依赖智谋。君主统一思想,因此民众不会各自为政,国家力量就会集中。国家力量集中,国家就强大;国家喜好空谈,国家就衰弱。
所以说,有千个从事农战的人,而有一个擅长《诗》、《书》辩论的人,那么千个人都会对农战懈怠。有百个从事农战的人,而有一个技艺高超的人,那么百个人都会对农战懈怠。
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战,是因为君主喜好空谈,官员失去了职责。
职责明确的官员才能治理国家,专注于一件事情的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而治理有序,这是王道的体现。因此说:王道在外,君主专注于一件事情而已。
现在君主们谈论才能和智慧,并据此任用官员,智慧的人会根据君主的好恶来制定政策,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因此,官员不稳定,国家混乱,空谈者无法约束。
这样,民众的欲望怎能不增多?土地怎能不荒芜?《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家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却不让它们守卫和战斗。国家依靠这十种东西治理,敌人来了必定会削弱,不来必定会贫穷。
国家摒弃这十种东西,敌人不敢来,即使来了也能击退;发动战争攻击,必定能取得胜利;按兵不动,必定会富强。国家喜好力量,就会难以攻破;难以攻破的国家就会强大;喜好辩论的国家,就会容易攻破,容易攻破的国家就会危险。
因此,圣明的君主不是能掌握万物,而是知道万物的关键。因此,他们治理国家,只需关注关键。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大多不关注关键。朝廷谈论治理,纷纷扰扰,急于相互改变。因此,君主被空谈迷惑,官员被空谈搞乱,民众懒惰而不从事农业。
因此,国内的人民都趋向于辩论、乐于学习,从事商业,学习技艺,逃避农战。这样,国家的衰败就不会远了。
国家有事时,学者们厌恶法律,商人善于变化,技艺的人不用,所以国家容易被打败。农民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多,所以国家贫穷危险。
螟虫、螣虫、蚼蠋、蠋虫在春天出生,秋天死去,一旦出现,民众就要几年不吃粮食。现在一个人耕种,而一百个人吃他的粮食,这就是螟虫、螣虫、蚼蠋、蠋虫的数量。
即使有《诗》、《书》,一个村庄一束,一个家庭一个成员,对治理国家也没有帮助,这不是改变现状的方法。因此,先王们把民众引导到农战。
因此说:百人耕种,一人居住的国家可以称王,十人耕种,一人居住的国家可以强大,半耕半居的国家就危险。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希望民众都从事农业。
国家不从事农业,就无法与诸侯争夺权力,力量不足。因此,诸侯会侵犯它的弱点,趁它衰弱时,侵占土地而不振作,无法自救。
圣人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让民众专心于农业。民众专心于农业,就会变得朴素而易于管理,容易守信并参与战斗。专心一致,就会减少欺诈而重视安居,专心一致,就可以奖赏和惩罚,专心一致,就可以对外用兵。
民众亲近君主、服从命令,是因为他们每天从事农业。民众不能被利用,是因为他们看到游说之士事奉君主可以尊贵自己,商人可以致富,技艺可以谋生。
民众看到这三者的便利和利益,就会逃避农业。逃避农业,就会轻视自己的居所。轻视居所,就不会为君主守卫和战斗。
治理国家的人,担心民众散乱而无法凝聚,因此圣人通过统一思想来凝聚民众。国家统一思想一年,国家就强大十年;统一思想十年,国家就强大百年;统一思想百年,国家就强大千年;千年强大的国家可以称王。
君主通过奖赏和惩罚来辅助统一思想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教育有固定的内容,政治有成效。
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因此不需要赏赐就能让民众亲近自己,不需要爵位就能让民众从事工作,不需要刑罚就能让民众为国捐躯。
国家危机,君主忧虑,游说者成群结队,对国家的安危没有帮助。国家危机和君主忧虑,是因为强敌和强大国家。
君主如果不能制服强敌、击败大国,就要加强防御,利用地形,凝聚民众力量,等待外部事务,然后才能消除隐患,实现王道。
因此,明君加强政治,统一思想,摒弃无用之物,阻止游说、学习无益之事的民众,专注于农业,然后国家才能富强,民众力量才能凝聚。
现在君主们都担心国家危险和军队弱小,却喜好空谈。游说者成群结队,言辞华丽,没有实际作用。君主喜好他们的辩论,不追求实际效果。
游说者得意洋洋,道路上的辩论纷繁复杂,成群结队。民众看到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获得王公大人的青睐,都去学习。
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国内外议论纷纷,小民喜欢这样做,大人也喜欢这样做。因此,民众中从事农业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
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就危险;从事农业的人危险,土地就会荒芜。学者成为风俗,民众就会放弃农业,从事辩论,高谈阔论。
放弃农业、游手好闲,用言辞相互夸耀,所以民众就会疏远君主而不臣服。这是贫穷国家和弱小军队的教育。
国家如果听信民众的言论,民众就不会从事农业。因此,只有明君知道喜好空谈不能强大军队、开拓土地,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时,才会专注于农业。
因此说:国家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业和战争,是因为君主喜好空谈,官员失去了职责。职责明确的官员才能治理国家,专注于一件事情的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而治理有序,这是王道的体现。因此说:王道在外,君主专注于一件事情而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农战-注解
官爵:指官职和爵位,是古代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农战:指农业和战争,是古代国家富强的基础。
巧言虚道:指花言巧语和虚假的言辞,没有实际内容。
劳民:指使人民过度劳累。
善为国者:指善于治理国家的人。
壹:指统一,专一。
仓廪:指仓库,储存粮食的地方。
《诗》、《书》:指《诗经》和《尚书》,是古代中国的经典文献。
外权:指外来的权力或影响。
要靡:指轻薄,不稳重。
商贾:指商人。
技艺:指手艺或技术。
豪杰:指有才能和胆识的人。
末货:指微小的财物。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指《诗经》、《尚书》、礼仪、音乐、善良、修养、仁爱、廉洁、辩论、智慧等儒家文化中的十种美德。
王道:指君王治国之道。
材能知慧:指才能、智慧和知识。
知虑:指知识和谋略。
辩说:指辩论和说服。
说者:指善于言辞的人。
游食者:指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
螟、螣、蚼蠋:指昆虫,比喻对国家有害的人。
乡:指地方。
束:指一束,一种计量单位。
员:指人。
归心于农:指使人民的心思都集中在农业上。
散而不可抟:指民心散乱,无法凝聚。
作壹:指统一思想,专一行动。
抟之:指团结起来。
强敌大国:指强大的敌对国家。
服强敌、破大国:指战胜强大的敌对国家。
修守备:指加强防御设施。
便地形:指利用地形优势。
抟民力:指凝聚民力。
外事:指对外事务。
王可致也:指可以成就王业。
强听说者:指喜欢听他人言辞的人。
辩说之人:指善于辩论的人。
游士:指游说之士,指那些四处游说的人。
成伍:指成群结队。
辈辈成群:指一代接一代地成群结队。
王公大人:指王侯贵族。
聚党与:指结党营私。
纷纷焉:指纷纷扰扰。
小民乐之:指普通百姓乐于接受。
大人说之:指贵族阶层也乐于接受。
游食: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言相高:指用言辞互相攀比。
离上而不臣:指背叛君主,不臣服于国家。
弱兵:指军队弱小。
辟土:指开拓土地。
明君:指明智的君主。
圣人之治国:指圣明之君治理国家。
作壹、抟之于农:指将国家治理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凝聚民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农战-评注
这段古文出自《商君书》,反映了古代中国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即强调国家治理应以农战为本,反对空谈和巧言虚道。以下是对每行的赏析: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这段话指出,君主劝民的方式是通过官爵,而国家兴旺的关键在于农战。然而,现在的人们追求官爵却不从事农战,而是用巧言虚道,这是劳民伤财的表现。劳民伤财的国家必然国力衰弱。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
这段话强调,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教育民众专注于一件事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官爵。因此,不追求官爵的人就不会被官爵所累。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会朴实,不会放纵。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民众看到通过专注于一件事情可以获得利益,就会选择专注。专注于一件事情,民众就不会偷懒,这样国家就会拥有更多的力量,从而变得强大。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这段话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人们认为可以通过避免农战来获得官爵,因此豪杰们纷纷改变职业,学习《诗》、《书》,追随外部势力,以求得显赫地位或官爵。而那些平庸之辈则从事商业和技艺,以规避农战。
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这种现象表明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民众以此作为教育,那么国家必将衰落。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
这段话指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仓库充实,也不会忽视农业;国家强大、民众众多,也不会沉溺于空谈。
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
这样,民众就会变得朴实,官爵也就不会轻易被巧取。
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
官爵不易得,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人,君主也就不会受到迷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
现在,境内的人们以及那些已经获得官爵的人,看到朝廷可以通过巧言辩论来获得官爵,因此官爵不再稳定。
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因此,他们要么曲意逢迎君主,要么考虑个人私利,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终导致权力被买卖。
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
曲意逢迎君主和卖官鬻爵,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爵禄和私利。
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
那些希望升迁的下级官员会说:‘只要多送财物,就能得到上级的青睐。’他们认为自己如果不送财物,就像用猫捉老鼠一样,肯定不会有希望;如果用感情去迎合上级,就像拉紧断绳去攀爬弯曲的树木一样,更加没有希望。
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升迁,那么我怎么能不动员众人,筹集财物来事奉上级,以求升迁呢?
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
百姓们说:‘我痛恨农业,先充实公仓,收余粮来养活亲人;为了君主,不顾生死而战斗,以尊重君主、安定国家。仓库空虚,君主地位低下,家庭贫穷。
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
那么不如去追求官职。亲戚朋友聚会,就更加忧虑了。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豪杰们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外部势力;平庸之辈从事商业和技艺,都是为了规避农战。
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如果民众以此为教育,那么粮食怎能不减少,军队怎能不削弱呢?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官法明确,因此不依赖智谋。
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
君主专注于一件事情,因此民众不会偷懒,这样国家力量就会凝聚。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国家力量凝聚就会强大,而那些喜欢空谈的国家则会衰落。
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所以说:在千名从事农战的人中,如果有一个人精通《诗》、《书》和辩论,那么其他九百九十九人都会对农战懈怠。
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在百名从事农战的人中,如果有一个人擅长技艺,那么其他九十九人都会对农战懈怠。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战才能尊贵。
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民众不从事农战,是因为君主喜欢空谈,官员失去了常态。
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
官员常态,国家就能治理好;专注于一件事情,国家就能富裕。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国家富裕且治理好,这就是君王的道路。
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所以说:君王的道路在于外部行动,自身专注于一件事情而已。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
现在,君主根据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员,那么智慧的人就会迎合君主的好恶,使官员制定政策来迎合君主的心意。
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因此,官员不稳定,国家混乱而不统一,辩论之人才无法治理。
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
这样,民众的欲望怎能不多?土地怎能不荒芜?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家有这十种东西,君主不让他们守卫和战斗。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
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治理,敌人来了就会削弱,不来就会贫穷。
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国家摒弃这十种东西,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使来了也会被打退;出兵攻打,一定能取得胜利;按兵不动,国家就会富裕。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国家喜好武力的人难以攻打,难以攻打的国家必然兴盛;喜好辩论的国家容易攻打,容易攻打的国家必然危险。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因此,圣明君主并不是能够了解所有事物,而是知道万物的关键。
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因此,他们治理国家,只需要关注关键。
今为国者多无要。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没有关键。
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
朝廷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情,纷纷扰扰,忙于相互改变。
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
因此,君主被空谈所迷惑,官员在言论上混乱,民众懒惰而不从事农业。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
因此,境内的民众都变得喜欢辩论、乐于学习,从事商业和技艺,规避农战。
如此,则不远矣。
这样,离国家灭亡就不远了。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国家有事时,学习的人厌恶法律,商人善于变化,技艺之人不用,因此国家容易被打败。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从事农业的人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多,因此国家贫穷危险。
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
就像那些春生秋死的螟、螣、蚼蠋一样,一旦出现,民众就会连续几年没有食物。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
现在一个人耕种,却有上百人依赖他的食物,这就像那些螟、螣、蚼蠋一样庞大。
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即使有《诗》、《书》,每个乡村有一份,每个家庭有一人,对治理国家也没有帮助,这不是改变现状的方法。
故先王反之于农战。
因此,古代圣王将民众引导到农战上。
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所以说:一百人从事农业,一个人居住的人可以称王;十人从事农业,一个人居住的人可以称强;一半从事农业,一半居住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
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希望民众从事农业。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国家不从事农业,就无法与诸侯争夺权力,力量就会不足。
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因此,诸侯会攻击国家的弱点,利用国家的衰弱,侵占土地,国家就无法振兴。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圣明君主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让民众的心思回归到农业上。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民众的心思回归到农业上,就会变得朴实而容易管理,可以信任他们守卫和战斗。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专注于一件事情,就会减少欺诈,重视居住,可以赏罚得当,可以用于对外。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民众亲近君主,愿意为他而死,是因为他们日夜从事农业。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
民众之所以不可使用,是因为他们看到游说之士侍奉君主可以尊贵自己,商人可以致富,技艺可以养家。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民众看到这三者的便利和利益,就会避开农业。
避农,则民轻其居。
避开农业,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
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轻视居住地,就一定不会为君主守卫和战斗。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
治理国家的人担心民众离散,无法凝聚,因此圣明君主通过专注于一件事情来凝聚民众。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国家专注于一件事情一年,就会强大十年;专注于十年,就会强大百年;专注于百年,就会强大千年;强大千年的国家就能称王。
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君主修订赏罚制度来辅助专注的教育,因此教育有常规,政治有成就。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君王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因此不需要赏赐就能让民众亲近君主,不需要爵禄就能让民众从事工作,不需要刑罚就能让民众拼死战斗。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
国家危难,君主忧虑,游说之士成群结队,这对国家的安危没有好处。
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
国家危难,君主忧虑,是因为强敌大国的威胁。
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
君主如果不能制服强敌、打败大国,就要加强防御,利用地形,凝聚民众的力量,等待外事的变化,然后才能消除祸患,实现君王的理想。
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因此,圣明的君主修订政策,专注于一件事情,去除无用之物,阻止那些浮夸的学习和淫逸的民众,引导他们从事农业,然后国家才能富裕,民众的力量才能凝聚。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
现在,世上的君主都担心国家的危险和军队的弱小,却强化游说之士。
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
游说之士成群结队,言语繁杂,辞藻华丽,却没有实际用处。
主好其辩,不求其实。
君主喜欢他们的辩论,却不去追求实际。
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
游说之士得意洋洋,道路上的辩论曲折多变,一代又一代地成群结队。
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民众看到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获得王公大人的青睐,于是都去学习。
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
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国内外进行游说,议论纷纷,小民喜欢,大人也赞同。
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因此,从事农业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
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
游手好闲的人多了,从事农业的人就会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减少了,土地就会荒芜。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
学习成为一种风气,民众就会放弃农业,从事辩论,高谈阔论,发表虚假的议论。
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
放弃农业,游手好闲,以言辞相高,因此不臣服于君主的人成群结队。
此贫国弱兵之教也。
这是导致国家贫穷、军队弱小的教育。
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
如果一个国家听信民众的言论,那么民众就不会从事农业。
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因此,只有明君知道空谈不能使军队强大、开拓土地,只有圣明君主治理国家时,才会专注于农业,凝聚民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