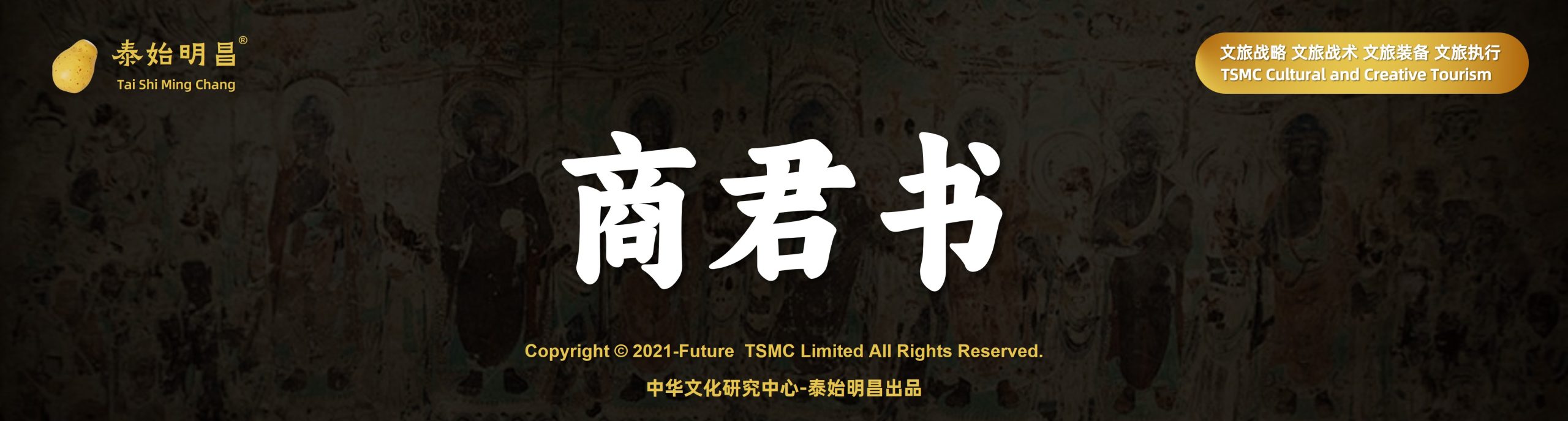作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代: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
内容简要:《商君书》是商鞅的法家思想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法律制度、军事战略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权力集中和严刑峻法的理论,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和社会运作,提倡法制至上的治理理念。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在秦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应用,最终对秦朝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成为法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修权-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君臣释法任私必乱。
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
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
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
文武者,法之约也。
故明主任法。
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
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
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
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
故法者,国之权衡也。
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
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
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
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
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
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
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
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
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
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
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
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
下离上者,国之‘隙’也。
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
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
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修权-译文
国家能够治理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法律,二是信任,三是权力。法律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任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掌握的,如果君主失去了这些,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如果君臣放弃法律而任由私心,必然会导致混乱。因此,制定法律明确分工,不因私心损害法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权力由君主独断独行,才能保持威严。民众相信君主的奖赏,事情就能成功;相信君主的刑罚,邪恶就不会产生。只有明智的君主重视权力,坚守信任,不因私心损害法律。所以,如果君主说了很多好话却不兑现奖赏,那么下面的人就不会效忠;如果经常发布严厉的命令却不执行刑罚,那么民众就会傲慢且不怕死。
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刑罚都是武治。文治和武治,都是法律的约束。因此,明智的君主会坚持法律。明智的君主不隐瞒事实叫做明智,不欺骗叫做明察。因此,奖赏要丰厚且可信,刑罚要严厉且必行;不忽视疏远的人,也不偏袒亲近的人,所以臣子不会隐瞒君主,下面的人也不会欺骗上面。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放弃法律而任由私心议论,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古代的圣王悬挂权衡,设立尺寸,至今仍然遵循这些法律,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如果放弃权衡而随意判断轻重,废弃尺寸而随意估计长短,即使再聪明,商贾也不会使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可靠的。所以,法律是国家权衡的标准。那些背离法律而任由私心议论的人,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尧不凭私心评价人的智慧、能力、贤能和有无德行;但世人并不都是尧。因此,古代的圣王知道不能任由私心议论,所以制定法律明确分工,符合标准的人给予奖赏,破坏公德的人予以惩罚。奖赏和惩罚的法律,不会失去公正,所以民众不会争斗。如果不因亲疏关系给予爵位和禄位,那么勤劳的臣子就不会抱怨;如果不因刑罚而疏远亲近的人,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亲近上面。所以,授予官职和爵位不因其劳绩,那么忠诚的臣子就不会被提拔;行赏和分配禄位不因其功绩,那么战士就不会被使用。所有臣子侍奉君主,大多是因为君主喜欢的事情。
君主喜欢法律,臣子就会依照法律侍奉君主;君主喜欢言论,臣子就会依照言论侍奉君主。君主喜欢法律,正直的人就会站在前面;君主喜欢言论,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在旁边。
公私分明,小人就不会嫉妒贤能,不贤的人也不会嫉妒有功的人。因此,尧和舜之所以能够治理天下,不是因为他们私占天下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治理天下;他们根据才能和德行选拔人才,并不是因为疏远父子关系或者亲近外人,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治理混乱的方法。因此,三王用道义来亲近人,五霸用法律来正视听诸侯,都不是因为他们私占天下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为了治理天下。因此,他们享有名声并且取得功绩,天下的人民都乐于接受他们的治理,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现在乱世中的君主和臣子,都自私地占据一国的利益和掌握一官之重,以便谋取私利,这就是国家危险的原因。因此,公私之间的交流,是存亡的根本。
如果废弃法律而喜欢私心议论,那么奸臣就会卖官鬻爵以谋取私利,官吏就会隐瞒下情而鱼肉百姓。俗话说:‘蛀虫多了,木头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就会倒塌。’所以,大臣们如果只顾私利而不顾民众,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与上面疏远。下面的人与上面疏远,就是国家的‘缝隙’。官吏如果隐瞒下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民众的‘蛀虫’。所以,如果国家有‘缝隙’和‘蛀虫’而不灭亡,那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明智的君主任用法律去除私心,那么国家就没有‘缝隙’和‘蛀虫’了。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修权-注解
法:法指的是法律、法规,是治国的基本准则,体现了君臣共同遵守的规则。
信:信指的是诚信、信任,君臣之间以及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
权:权指的是权力,特别是君主的权力,是君主独断专行的能力。
君臣:君臣指的是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赏:赏指的是奖励,是对功绩的认可和激励。
刑:刑指的是惩罚,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
文武:文武指的是文化和武力,是治国之道的两个方面。
明主:明主指的是明智的君主,能够明智地治理国家。
尧:尧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以德治天下著称。
先王:先王指的是古代的贤明君主,是后世的典范。
权衡:权衡是古代用来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比喻为衡量事物轻重的方法。
尺寸:尺寸是古代的长度单位,比喻为标准。
私议:私议指的是个人的意见或私人的观点。
爵禄:爵禄是古代的官职和俸禄,是官员地位的象征。
劳臣:劳臣指的是为国家辛勤工作的臣子。
战士:战士指的是国家的军队成员。
端直之士:端直之士指的是正直无私的士人。
毁誉之臣:毁誉之臣指的是善于阿谀奉承、左右逢源的臣子。
小人:小人指的是品德低劣的人。
不肖者:不肖者指的是品行不端的人。
贤能:贤能指的是有才能和德行的人。
不肖:不肖指的是不贤德、不才干的人。
义:义指的是正义、道义,是行为准则。
法正:法正指的是依法行事,使诸侯遵守法律。
私利:私利指的是个人的利益。
公私之交:公私之交指的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隙:隙指的是缝隙,比喻国家内部的矛盾和裂痕。
蠹:蠹指的是蛀虫,比喻危害国家的人或事。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商君书-修权-评注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此句开篇点明了治国之三大要素,即法律、信用和权力。其中,法律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用是君臣共同建立的,而权力则是君主独自掌握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此段进一步阐述了法律、信用和权力的具体含义,强调了君主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君主失守将带来的危险。
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此句指出,君臣若放弃法律而任由私欲,必将导致混乱。因此,明确法律界限,不因私欲而损害法律,才能实现治理。
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此段强调了君主在权力和信用方面的作用,指出君主若能独断专行,民众对其赏罚有信心,则国家事务得以顺利进行。
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此段提出了明君的标准,即爱权、重信、不私害法。同时,指出若君主言而无信,则民众将不服从。
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此段将赏罚与文武相提并论,强调了赏罚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明君应重视法律。
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此段进一步阐述了明君的治国理念,即公正无私,赏罚分明。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此句指出,当世治国者多忽视法律,任由私议,导致国家混乱。
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此段以权衡和尺寸为例,说明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放弃法律必将导致混乱。
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此段进一步强调了法律作为国家权衡的重要性,并指出古代先王深知私议的危害,因此制定明确的法律。
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此段阐述了赏罚、爵禄、官职等方面的原则,强调了君主应以法为重,臣子应以法事君。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此段指出,公私分明是治国之根本,并引用尧、舜的例子说明,君主应以天下利益为重,而非私欲。
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此段进一步阐述了三王、五霸的治国理念,指出他们以天下为重,而非私欲,从而使得国家繁荣昌盛。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此段总结了公私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废法度、好私议必将导致国家衰败,而明君应以法为重,去除私欲,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