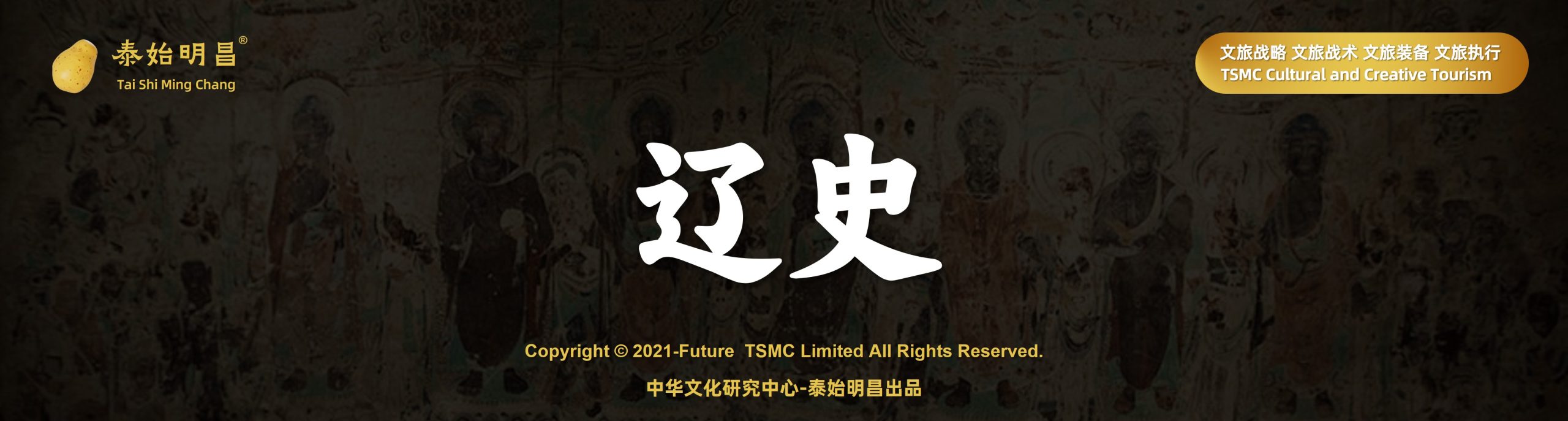作者: 沈括(1031年-1095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辽史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学、文学与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尤其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
年代:成书于宋代(约11世纪)。
内容简要:《辽史》是宋代史学家所编写的关于契丹辽朝历史的史书,详细记录了辽朝的兴衰历程。书中内容涉及辽朝的建立、政治制度、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后的一个强大政权,辽史不仅记载了辽朝的历代帝王与重要事件,还涉及了辽朝与宋朝、金朝等其他朝代的互动。通过对辽朝历史的详细阐述,《辽史》为后世研究契丹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等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辽史-列传-卷三十三-原文
◎文学上
○萧韩家奴 李澣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
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
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骁崇儒之美。
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蒐浯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
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
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
统和十四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
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
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
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
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
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
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
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
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
帝大笑。
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
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何害可以止?’
韩家奴对曰: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
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
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
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
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
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
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
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
富者从军,贫者侦候。
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
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
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
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
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
臣谓不然。
阻卜诸部,自来有之。
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
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
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
统和间,王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
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
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
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
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
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
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
得不为益,舍不为损。
国家大敌,惟在南方。
今虽连和,难保他日。
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
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
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
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
叛则讨之,服则抚之。
诸部既安,必不生衅。
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
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
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
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帑廪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
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
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
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
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
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
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
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
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
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
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
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兵亦然。
譬如一杯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
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
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
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
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
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
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
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
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
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
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
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
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
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
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
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
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
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
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
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
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
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
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
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
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
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
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
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
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
帝见,命去之。
韩家奴既出,复书。
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
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
韩家奴以穆宗对。
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
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
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
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
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
以善治闻。
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
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
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
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涣不定,澣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
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
时澣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
澣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
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
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
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
及抵上京,帝欲杀之。
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
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
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
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
诏从之。
文成以进,上悦,释囚。
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
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
李澣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辽史-列传-卷三十三-译文
在文学方面,
萧韩家奴 李澣
辽国兴起于松漠地区,太祖用兵治理内地,对于礼制文化的事情本来就没有闲暇顾及。等到太宗攻入汴京,把晋国的图书、礼器运回北方,这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制度。到了景宗、圣宗年间,科举制度开始兴起,士人中有从下级官员提拔为侍从的,崇尚儒学的风气日益浓厚。但风气刚劲,三面邻敌,每年以搜捕盗贼为务,而典章文物,与古代相比还有所欠缺。然而两百年的基业,如果不是几位君子加以整理,后世又怎能考究和叙述呢?因此撰写了《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年轻时就爱好学习,二十岁时到南山读书,广泛阅读经史,通晓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开始做官。家中有一头牛,不听使唤,他的奴仆得到好价钱卖掉了它。韩家奴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误人子弟,这不是我所希望的。’于是他直接取回牛。二十八年,担任右通进,主管南京栗园。重熙初年,参与管理三司使事务。四年,升任天成军节度使,调任彰愍宫使。皇帝与他交谈,认为他有才,任命他为诗友。曾经随意地问他说:‘你在外面有什么特别的见闻吗?’韩家奴回答说:‘我只知道炒栗子:小的熟了,大的必然是生的;大的熟了,小的必然是焦的。如果大小都熟了,这才算是完美的。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因为他曾经掌管栗园,所以借炒栗子来讽谏。皇帝大笑。下诏让他写《四时逸乐赋》,皇帝认为写得很好。
当时皇帝下诏让天下人谈论治国之道的关键,制问:‘徭役没有加于旧有,征伐也不常有,年谷已经丰收,国库已经充实,但百姓仍然很困苦,难道是官吏们懈怠、百姓们懒惰吗?现在的徭役哪一项最重?哪一项特别痛苦?哪些地方可以减免,才能对百姓有益?补充徭役的方法可以如何恢复?如何才能阻止盗贼的侵害?’韩家奴回答说:
我观察到近年以来,高丽尚未臣服,阻卜部族还很强盛,战守的防备工作确实不能停止。最近选派富裕的百姓防守边疆,自己准备粮食。道路崎岖,动不动就耽误岁月;等到了驻防地,费用已经超过一半;只有一头牛一辆车,很少有能返回的。那些没有壮丁的家庭,需要支付双倍的租金,人们害怕劳累,半途而逃,所以守边士兵的粮食常常不够。向别人借贷,利息是十倍,甚至有卖掉孩子、割掉田地也还不起的。有的逃避徭役不回来,在军队中死去,就又补充年轻的壮丁。在鸭绿江以东,守边的徭役大致就是这样。何况渤海、女真、高丽联合起来,不时地进行征讨。富人从军,穷人负责侦察。再加上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大概是形势所迫的。
现在最重的徭役,莫过于西边的守卫。如果没有西边的守卫,即使遇到荒年,困苦也不会如此严重。如果能将西边的守卫移至较近的地方,那么往来就不会劳累,百姓也不会有深重的祸患。有人认为迁移并不方便:一是会损害威名,二是会招来侵略,三是会放弃耕牧之地。我认为并非如此。阻卜各部族,自古以来就有。过去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们分散居住,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有来来往往的抢劫。等到太祖西征,直到流沙,阻卜看到风势,全部投降,西域各国都愿意来进贡。于是迁移部落,在国内设立三部,以增加我国的力量,不建城池,不设守兵,阻卜历代不敢侵犯。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兵西域,开拓的土地已经非常遥远,归附的人也很多。此后一个部落如果叛乱,邻近的部落就会讨伐它,这样可以使各部共同制约,这正是驾驭远方人的方法。等到城可敦,开辟了几千里土地,西北地区的百姓,徭役日益增加,生计日益枯竭。紧急情况不能救助,叛服也不稳定。空有广袤土地的名号,而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如果贪图土地不止,渐渐就会导致国家虚耗,其祸患无法言尽。何况边疆的情况不能过于信任,也不能突然断绝。能得到的好处,舍弃也不会造成损失。国家的大敌,只在南方。现在虽然联合,难以保证将来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南方有变故,驻防辽远,士兵难以迅速支援。我们进攻敌人就退却,我们撤退敌人就进攻,这不能不考虑。
现在太平已经很久了,正可以恩惠结交各部,赦免罪行,归还土地,将守兵内迁以增加防御,对外明确约束以正疆界。每个部落都设立首领,每年上交贡品。叛乱就讨伐,顺服就安抚。各部族一旦安定,就不会生事。这样,我虽然不能保证他们长久不变,但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侵扰。
有人说放弃土地会损害威名,但不知道耗尽财富,为了贪图无用的土地,使得那些小部族敢于与大国对抗,万一有败,损失威名岂会浅?又有人说,肥沃的土地不能轻易放弃。我认为土地虽然肥沃,但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犯,就不可避免地要内迁,怎么可以指为我国的土地而吝惜呢?
国库虽然随着各部族而存在,这只是为了解决部族人民的燃眉之急,是一种局部的恩惠,不能惠及天下。如果想要惠及天下,就应该知道百姓困苦的原因,并堵塞这些漏洞。节制游宴,简化驿站,减轻赋税,戒除奢侈。几年之后,困苦的人可以得到缓解,贫穷的人可以变得富裕。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的保卫者。军队调动不当,就会旷废军役,调动就会损害国家的根本。而且各部族都有补充徭役的方法。过去实行补充徭役时,居住和行军的人,都是富裕的,所以世代从军,容易更换。近年来边疆危机频繁,百姓多贫困,既不能承担徭役,补充又随时出现空缺。如果没有富裕的家庭,中产阶级就要承担。时间越长,贫困越严重,所以代替徭役就越困难。不仅补充徭役是这样,边疆守军也是如此。比如一杯土,怎么能填满深沟呢!想要长久方便,不如让远征的疲惫士兵回到故乡,减轻他们的徭役,让每个人都充足,这样补充徭役的方法就可以恢复。
我又听说,自古以来有国家的,不能没有盗贼。近年以来,百姓生活困苦,利于盗窃,良民常常变成凶暴之徒。更严重的是杀人无顾忌,甚至有逃入山林水泽的,成为作乱的首恶。所谓民因困苦而成为盗贼的,确实如同圣上的忧虑。现在想要根除盗贼的根源,希望陛下减轻徭役,让百姓专心务农。衣食充足之后,百姓就会安于教化,重视法律,刑罚就会很少使用。我听说唐太宗问群臣如何治理盗贼,大家都说:‘严厉的刑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增多,是因为赋税无度,百姓无法生活。现在我内省自己的欲望,减少外出游玩,使全国安静,那么盗贼自然会停止。’从这一点来看,盗贼的多少,都是由衣食的丰俭,徭役的轻重决定的。
现在应该将可敦城迁移到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相互支援。撤销黑岭二军,将开州、保州都隶属于东京。增加东北守军和南京总管的兵力。加强修建壁垒,守望相助,修缮楼橹,疏通城隍,作为边防。这是现在的紧急事务,希望陛下考虑。
提升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皇帝还下诏告诉他:‘文章的职务,是国家的光辉,不是有才能的人不用。因为你的文学才华,是当代的大儒,所以授予你翰林之职。我的起居,都要用实录来记录。’从此他日益受到亲近信任,每次进宫侍奉,皇帝都会赐坐。遇到喜庆的日子,皇帝与他饮酒赋诗,相互酬答,君臣关系非常融洽。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在玩笑中也不忘规劝。
韩家奴被提拔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皇帝还下诏告诉他:‘文章的职务,是国家的光辉,不是有才能的人不用。因为你的文学才华,是当代的大儒,所以授予你翰林之职。我的起居,都要用实录来记录。’从此他日益受到亲近信任,每次进宫侍奉,皇帝都会赐坐。遇到喜庆的日子,皇帝与他饮酒赋诗,相互酬答,君臣关系非常融洽。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在玩笑中也不忘规劝。
十三年春天,上书说:‘我听说先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运中断。自从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开始,皇位才稳定下来。然而历代皇帝都朴实无华,没有尊称。我认为三皇的礼制文化还不完备,和遥辇氏一样。后来的君主用礼乐来治理天下,崇尚根本,追溯远祖的意义也开始兴起。最近唐高祖建立了先祖庙,尊称四代先祖为皇帝。过去我太祖代替遥辇即位,制定了文字,修订了礼法,建立了天皇帝的名号,建造宫殿以显示威严,兴利除弊,统一了海内。此后历代圣君相继,从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曾加封,天皇帝的先祖夷离堇的鲁还是以名来称呼。我认为应该依照唐代的典制,追尊四代先祖为皇帝,这样陛下的大业就有光彩,失落的文化就能复兴了。’上书奏上,皇帝采纳了,开始实行追封玄、德二祖的礼仪。
韩家奴每次见到皇帝打猎,总是劝谏。恰逢有官员上奏说在秋山打猎时,熊虎伤死了数十人,韩家奴将这些情况记录在册。皇帝看到后,命令去掉这些记录。韩家奴离开后,又写了一封信。另一天,皇帝看到信后说:‘史书的笔法应当如此。’皇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谁是贤明的君主?’韩家奴回答说:‘穆宗。’皇帝感到惊讶说:‘穆宗好酒,喜怒无常,对人视如草芥,你为什么说他是贤明的?’韩家奴回答说:‘穆宗虽然暴虐,但减轻了徭役和赋税,人民生活得快乐。在穆宗的时代,无罪而遭杀戮的人,还没有超过这次秋山打猎死者的人数。所以我认为穆宗是贤明的。’皇帝沉默不语。
皇帝下诏让耶律庶成记录遥辇可汗到重熙年间的所有事迹,编纂成二十卷,进呈皇帝。十五年,皇帝再次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明白礼义,端正法度。我朝兴起,世代都有明德,虽然中外都向化,但是礼书还没有编写,无法向后世展示。你可以和庶成参考古代,制定礼典。如果遇到疑问,可以和北、南院共同商议。’韩家奴接受诏令后,广泛查阅经籍,从天子到平民,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违背古制的,撰写成三卷,进呈皇帝。皇帝又下诏翻译各种书籍,韩家奴想要皇帝知道古今的成败,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当时皇帝因为韩家奴年老,不便朝见,任命他为归德军节度使。韩家奴以善于治理而闻名。皇帝派人去慰问,韩家奴上表表示感谢。后来被召回修订国史,去世时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流传于世。
李澣,最初在晋朝担任中书舍人。晋朝灭亡后归附辽朝,在太宗去世、世宗即位之际,国家动荡不安,李澣和高勋等十余人被留在南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到上京,李澣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后,李澣多次升迁,成为工部侍郎。当时李澣的哥哥李涛在汴京担任翰林学士,秘密派人召回李澣。李澣接到信后,假托求医南京,换上便服在夜间出逃,想要逃回汴京。到了涿州,被巡检人员抓获,被送回南京,被下放到官府。李澣趁狱吏熟睡,用衣带自缢;但没有死,防范更加严格。被囚禁押送至上京,他跳入潢河中流,被铁链拉住,还是没有死。到达上京后,皇帝想要杀他。当时高勋已经担任枢密使,救了他。高勋多次向皇帝进言说:‘李澣本来并没有辜负恩情,因为母亲年事已高,急于探望而犯罪。而且李澣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现在是少有的才子,如果留下他掌管文辞,可以增加国体的光辉。’皇帝的怒气稍微缓解,但还是命令将他软禁在奉国寺,共六年,遭受了极大的苦难。恰逢皇帝想要建立《太宗功德碑》,高勋上奏说:‘没有比李澣更合适的人来撰写。’皇帝下诏同意。文章完成后进呈,皇帝很高兴,释放了他。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去世。
评论说:统和、重熙年间,致力于修文治,而韩家奴的对策,洋洋洒洒数百言,大致可以应用于实际事务,也是辽朝的晁、贾啊。李澣虽然以文学成就著称,但他的进退不足以评论。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辽史-列传-卷三十三-注解
辽:指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存在于907年至1125年。
太祖:太祖通常指一个朝代的建立者,这里指的是辽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
太宗:指辽朝的第二位皇帝耶律德光。
汴:指北宋的都城开封。
科目:指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
侍从:指皇帝身边的官员,负责陪侍皇帝。
崇儒:指尊崇儒家学说,儒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流派。
蒐浯:指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
典章文物:指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遗产。
涅剌部:指辽朝的一个部族。
中书令:指中书省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宰相。
弱冠:指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
南山:指辽朝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南部。
经史:指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
通:指精通。
粮糗:指粮食。
徭役:指古代中国的一种劳役制度。
征伐:指战争。
帑廪:指国库。
防边:指防御边疆。
屯所:指驻军的地方。
丁:指成年男子,古代中国以丁口为征税和徭役的单位。
佣僦:指雇佣劳动力。
物故:指死亡。
阻卜:指辽朝时期的一个民族。
城可敦:指辽朝的一个地名。
城邑:指城市。
城障:指防御工事。
酋长:指部落的首领。
职贡:指向中央政府进贡。
盘游:指游宴。
驿传:指古代传递信息的驿站。
赋敛:指征税。
教化:指道德教育。
翰林都林牙:指翰林院的高级官员。
起居:指皇帝的日常生活。
实录:指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官方记录。
遥辇可汗洼:遥辇可汗洼是辽朝的一个早期统治者,他是辽朝建立者耶律阿保机的父亲。在这里,指的是辽朝先祖的一个时期。
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夷离堇是辽朝的一种官职,雅里是人的名字,阻午是其称号。这里指的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三皇:三皇是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位神话时代的帝王,即伏羲、神农、黄帝。
礼文:礼文指的是古代的礼仪制度和文化。
先庙:先庙是指供奉祖先的庙宇。
天皇帝:天皇帝是辽朝皇帝的称号之一,表示皇帝具有天命。
宫室:宫室指的是皇帝的宫殿。
崇本追远:崇本追远是指尊敬祖先,追溯根源。
唐高祖:唐高祖李渊,唐朝的开国皇帝。
礼乐治天下:礼乐治天下是指通过礼仪和音乐来治理国家。
混一海内:混一海内是指统一全国。
累圣:累圣是指连续几代的皇帝。
唐典:唐典是指唐朝的典章制度。
追崇:追崇是指对已故的尊贵人物进行追念和尊崇。
玄、德二祖:玄、德二祖是指辽朝的两位祖先。
册:册是指皇帝对某人的正式封号或任命。
猎:猎是指打猎,古代皇帝常以此作为娱乐活动。
秋山:秋山可能指的是秋季打猎的山地。
熊虎伤死:熊虎伤死指的是在打猎过程中被熊虎伤害致死的人。
册书:册书是指记录重要事件的官方文书。
史笔:史笔是指史书的笔法,即史书的写作风格。
贤主:贤主是指贤明的君主。
穆宗:穆宗是指辽朝的穆宗耶律璟,他在位期间以嗜酒和喜怒无常著称。
省徭轻赋:省徭轻赋是指减轻赋税和徭役。
天皇帝之考:天皇帝之考指的是天皇帝的父亲,即辽朝的夷离堇。
鲁犹:鲁犹可能是指夷离堇的一个称号或名字。
礼典:礼典是指关于礼仪的典籍。
经籍:经籍是指经典书籍。
庶人:庶人是指平民百姓。
情文制度:情文制度是指符合实际情况的礼仪制度。
不缪于古:不缪于古是指不违背古代的礼仪制度。
通历:通历是一部历史年表。
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政论集。
五代史:五代史是指五代时期的历史。
朝谒:朝谒是指臣子朝见皇帝。
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节度使是辽朝的一个官职。
羁留:羁留是指被拘留或扣留。
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古代皇帝的文学顾问。
工部侍郎:工部侍郎是古代官职,负责工程建设。
翰林学士涛:翰林学士涛可能是指李澣的兄弟。
徼巡者:徼巡者是指负责巡逻的官员。
械:械是指用铁链等物拘束。
奉国寺:奉国寺是辽朝的一座寺庙。
太宗功德碑:太宗功德碑是为纪念辽太宗耶律德光而立的碑。
枢密使:枢密使是辽朝的一种高级军事官职。
省觐:省觐是指回家探望父母。
《六义集》:《六义集》是韩家奴的一部著作。
统和:统和是辽朝的一个年号。
重熙:重熙是辽朝的一个年号。
晁、贾:晁、贾可能是指辽朝的两位有才学的官员。
词章:词章是指文学和文章。
进退:进退是指官员的升迁和降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辽史-列传-卷三十三-评注
这段古文描述了辽朝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辽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
首先,文中提到的‘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表明了辽朝的历史渊源和兴衰变迁。作者通过追溯先祖的功绩,强调了追崇先祖的重要性,体现了对历史传统的尊重。
‘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这句话描绘了辽朝建立的过程,强调了夷离堇雅里在建立辽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反映了辽朝初期的政治形态和社会风貌。
‘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表明了辽朝在文化上的继承和发展。作者认为,辽朝应该学习唐代的礼乐制度,以提升国家的文化品位。
‘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这句话展示了辽朝太祖的治国理念,即通过制度建设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
‘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反映了辽朝历代皇帝在位期间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天皇帝称号的演变。
‘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这句话体现了作者对辽朝未来发展的期望,即通过追崇先祖,提升国家地位。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表明了韩家奴的忠诚和责任感,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体现了辽朝士人的政治立场。
‘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这一段描写了韩家奴坚持原则的精神,他不顾皇帝的命令,坚持自己的观点。
‘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这句话反映了辽朝皇帝对贤主的评价标准,以及韩家奴的政治观点。
‘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这一段对话揭示了韩家奴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这句话说明了辽朝对历史的重视,以及对国家历史的整理。
‘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这一段描述了韩家奴在文化上的贡献,他通过对经籍的研究,为辽朝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这句话反映了辽朝对老年人的尊重,以及对地方治理的重视。
‘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涣不定,澣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这一段描述了李澣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这一段描写了李澣的坚韧和毅力,他在面对困境时,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这句话反映了辽朝的政治斗争,以及高勋在其中的作用。
‘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这一段描述了李澣在奉国寺的遭遇,以及他在其中的坚韧。
‘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这句话反映了李澣在文化上的贡献,以及他在辽朝的地位。
‘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这一段描述了李澣在文化上的成就,以及他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这一段总结了韩家奴和李澣在辽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同时也反映了辽朝在文化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