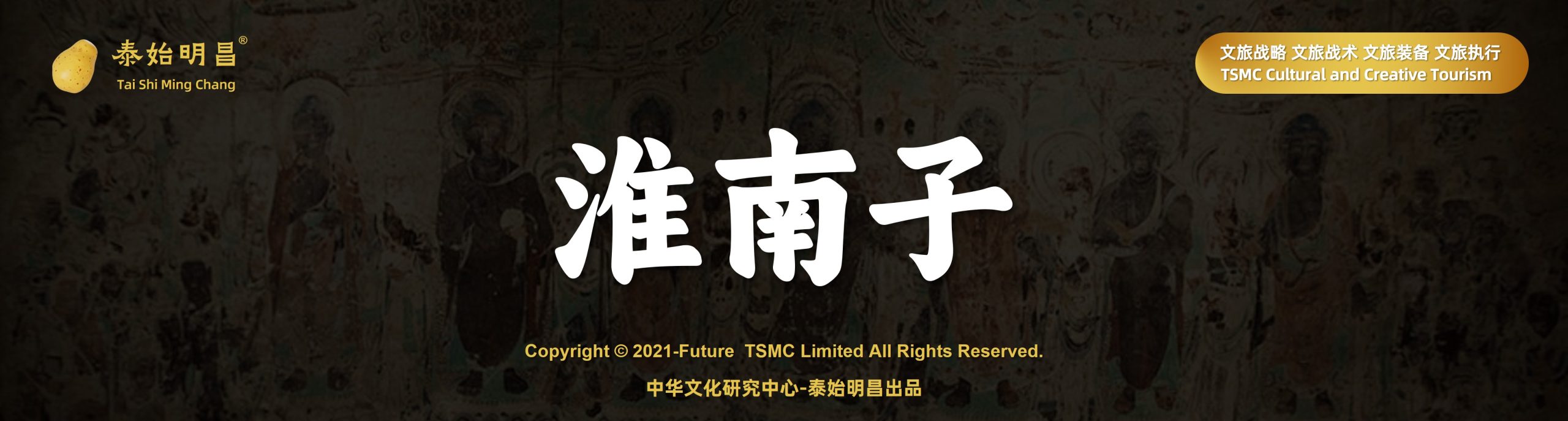作者: 刘安(约公元前179年-前122年),西汉时期的王子,封号淮南王。刘安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同时在道家哲学上也有卓越贡献。淮南子是他主编的集大成之作,融合了道家思想、儒家学说和兵法智慧。
年代:成书于西汉(约公元前2世纪)。
内容简要:《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下学者所编著的哲学与政治著作,涵盖了道家、儒家、法家、阴阳五行等多个思想流派的理论。书中系统阐述了宇宙、自然、人生的奥秘,提倡顺应自然、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全书共计21篇,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经济、伦理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淮南子》提出了很多治国理政的理论,如“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和“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的结合。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考。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淮南子-诠言训-原文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
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
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
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
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
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
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
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
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
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
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
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
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
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
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
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貁之捷来措。
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
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
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尝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
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
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似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
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
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
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
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
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
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
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
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节欲之本,在于反性。
反性之本,在于去载。
去载则虚,虚则平。
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
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亲,多知为败,毋亲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
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
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
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
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
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坺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
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
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者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
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
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
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
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
犹尊君也。
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
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
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
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
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
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
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
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
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
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
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
祸之至也,百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
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
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
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
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
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歧周而天下移风。
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
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
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
故秦胜乎戎而败乎骰,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
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
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
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
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
不豫谋,不弃时。
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
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祸,外无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
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
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
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
法修自然,己无所与。
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
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
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
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
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
其智也,皆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
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
章人者,息道者也。
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
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
欲尸名者必为善。
货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
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
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
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要中。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獘身。
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
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
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
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免于累矣。
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
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
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
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
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
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
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
故虽贤王,必待遇。
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
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诣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
故无为而自治。
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利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
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叵内治而待时。
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
事以玉帛,则货弹而欲不餍;卑体婉辞,则谕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
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
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
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
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
夫无为,则得于一也。
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
一身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
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衙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
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
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搪博,未有能者也。
独任其智,失必多。
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偩而辞助。
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
故好勇,危术也。
好与,则无定分。
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
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
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
故好与,来怨之道也。
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
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
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
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
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
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
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
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
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
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
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
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飱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
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
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瘤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
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滇而尘垢弗能污也。
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
故奈把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铃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
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
非藏无形,孰能形!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
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
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
此两者常在久见。
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
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
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
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
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
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萧有音,弗吹无声。
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
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
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
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
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
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
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
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
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
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
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
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
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
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
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
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
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
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
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干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仅愁人。
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
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
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
道胜,则人无事矣。
圣人无屈奇之眼,无瑰异之行,眼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
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
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
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
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 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
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
驰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
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
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
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
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
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
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
周公骰蠕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
匹夫百晦一守,不逞启处,无所移之也。
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
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
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
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
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
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
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
放 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
今与人卞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
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
两人相斗,一赢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
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
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瞎:此之谓狂。
有祸则础,有福则赢,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
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
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易故能天,简故能地。
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心有忧者,筐床袄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芋弗能乐也。
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
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
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
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
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
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
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
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
乱则降北,辩则本贼。
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
《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
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
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
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以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
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
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
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凛,见所始则知终矣。
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
圣人之接物,千变万化,必有不化面应化者。
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诉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
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
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
天道无亲,唯德是与。
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
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
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
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
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
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
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
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
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
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
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
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
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
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
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淮南子-诠言训-译文
与天地同源,混沌未分的状态叫做原始的朴质,还未形成具体事物时,称之为太一。虽然同出一源,但各自的表现不同,有鸟、有鱼、有兽,称之为分化的万物。按照类别来区分,事物按照群体来分类,生命和命运各不相同,但都显现于现实之中。它们被隔开而不相通,分化成万物,没有人能追溯到它们的根源,因此,活动时称之为生,死亡时称之为穷尽,都是因为它们是万物的一部分,而不是不成为万物的一部分而成为万物的一部分,成为万物的一部分的人已经消失在万物之中。
追溯古代的太初,人从无中生,在现实中有形,有形之后被物质所制约。能够返回到它的起源,就像还没有形成形状一样,称之为真人。真人是不曾从太一中分化出来的。圣人不会成为名声的奴隶,不会成为谋略的仓库,不会成为事务的责任者,不会成为智慧的统治者,隐藏在无形之中,行动不留痕迹,游走不留痕迹。不会成为福气的先导,不会成为祸患的源头,守护在虚无之中,行动是出于不得已。想要福气的人可能会招致祸患,想要利益的人可能会遭受损害。因此,无为而宁静的人,如果失去了宁静就会变得危险;无事而治理的人,如果失去了治理就会变得混乱。星星排列在天空中而明亮,因此人们指着它们;义理排列在德行之中而显现,因此人们看到它们。人们所指的,动起来就有规则;人们所看的,行动起来就有痕迹。动有规则就有言语,行有痕迹就有议论,因此圣人隐藏在无形之中,行动在无为之中。
王子庆忌死于剑,后羿死于桃木棒,子路在卫国被杀,苏秦死于口舌。没有人不珍惜他所拥有的,而轻视他所缺乏的,然而他们都沉溺于他们所珍视的,而极端地追求他们所轻视的,所珍视的是有形的,所轻视的是无形的,所以虎豹之强来射杀,猿猴之捷来捉拿。人如果能珍视他所轻视的,轻视他所珍视的,就可以谈论至高的道理了。
自信的人不会因为赞誉或诽谤而改变,知足的人不会因为权势和利益而诱惑,因此通达于自然情感的人,不会追求自然所没有的东西;通达于命运情感的人,不会担忧命运所无法改变的事情;通达于道的人,万物都无法扰乱他的和谐。詹何说:‘从未听说过身体治理而国家混乱的,也从未听说过身体混乱而国家治理的。’如果规矩不正,就不能用来画方;如果圆规不正,就不能用来画圆;身体是事物的规矩,从未有过扭曲自己却能端正他人的人。探究天命,治理心术,理顺好恶,适应情感,那么治理之道就通了。探究天命就不会对祸福感到困惑,治理心术就不会对喜怒感到迷茫;理顺好恶就不会贪图无用之物,适应情感就不会让欲望超过节制。不困惑于祸福就会动静遵循道理,不迷茫于喜怒就会赏罚公正,不贪图无用之物就不会用欲望损害本性,欲望不超过节制就会修养本性知足。这四者,都不需要从外界寻求,也不需要依赖他人,反观自己就能得到。
天下不能仅仅依靠智慧来治理,不能仅仅依靠事务来治理,不能仅仅依靠仁德来依附,不能仅仅依靠强权来胜利。这五者都是人才,德行不深厚,就不能成就其中之一。德行确立之后,这五者就没有危险,这五者显现之后,德行就没有地位了。因此,得道的人即使愚笨也足够,失道的人即使聪明也不足够。渡水而不懂得游泳,即使强大也必然会沉没;懂得游泳的人,即使瘦弱也一定能成功;更何况是依靠船只航行呢!
治理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安宁。使民众安宁的根本,在于满足他们的需求。满足需求的根本,在于不剥夺他们的时间。不剥夺时间的基础,在于减少事务。减少事务的基础,在于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的基础,在于回归本性。回归本性的基础,在于去除负担。去除负担之后就会变得虚空,虚空就会变得平和。平和是道的本质;虚空是道的居所。能够统治天下的人,必然不会失去他的国家;能够拥有国家的人,必然不会失去他的家庭;能够治理家庭的人,必然不会忽视自己的身体;能够修养身体的人,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心灵;能够探究心灵的人,必然不会损害自己的本性;能够保全本性的人,必然不会对道感到困惑。因此,广成子说:‘谨慎地守护内在,严密地封闭外部而亲近他人,知识太多会带来失败,不要亲近不要听从,保持精神上的宁静,身体自然会端正。不能了解自己却能了解他人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因此,《易经》说:‘封闭口袋,既无过错也无赞誉。’能够成就霸王者,必然是能够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必然是强大的人;能够强大的人,必然是利用人力的人;能够利用人力的人,必然是得到人心的人;能够得到人心的人,必然是自我满足的人;能够自我满足的人,必然是柔弱的人。强大的人战胜不如自己的人,到了与对方相同的时候就会遇到阻碍;柔弱的人战胜超过自己的人,他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因此,能够用众人的不足来成就大胜利的,只有圣人能够做到。
擅长游泳的人,不需要学习划船就能使用它;强壮的人,不需要学习骑马就能居住在它。轻视天下的人,身体不被物质所累,因此能够处之泰然。太王亶父住在邠地,狄人攻打他,用皮币珠玉来贿赂他,但他不听,于是辞退了老人并迁移到岐周,百姓带着幼儿扶着老人跟从他,最终建立了国家。按照这个意思,四代而有天下,不是很合适吗!不把天下当作目标的人,一定能够治理天下。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而贵天,厌弃文饰和法度,治理官民的是官员,君主不需要亲自处理。就像尊重君主一样。开垦土地的是后稷,治理黄河开凿长江的是大禹,审理案件制定中道的是皋陶,有圣名的是尧。因此,能够得道来统治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能力,也一定能够使有能力的人为自己所用。不能得道的人,即使技艺再多,也没有益处。用空船在江中渡河,有一艘空船从另一边来,碰撞后翻覆,即使有怨恨之心,也一定不会有怨恨的表情。如果船上有一个人,一个人让他张开,一个人让他收拢,多次呼唤而不回应,一定会用丑陋的声音跟在他后面。之前不生气而现在生气,之前是空的而现在是有形的。人如果能以虚空的心态游走于世间,谁又能指责他呢!
放弃道而依赖智慧的人一定会危险,放弃计算而依赖才能的人一定会困顿,有因为欲望过多而灭亡的,没有因为无欲而危险的;有因为欲望治理而混乱的,没有因为守常而失去的。因此,智慧不足以避免祸患,愚笨不足以达到安宁。坚守自己的本分,遵循自然的道理,失去时不忧虑,得到时不喜悦,因此成就的不是自己所追求的,得到的不是自己所求的。进入时不索取,出去时不给予,根据春天生长,根据秋天凋零;所生长的不去感恩,所凋零的不去怨恨,就接近于道了。
圣人不会做那些会被非议的行为,也不会因为别人非议自己而憎恨他们;修养足以获得赞誉的品德,却不去追求别人的赞誉。
不能阻止灾祸不发生,相信它不会主动找上门来;不能确保福气一定会到来,相信它不会主动降临。
灾祸到来时,它有无数种可能的原因,所以即使陷入困境也不忧愁;福气到来时,它并非出自我们的追求,所以即使通达也不骄傲。
明白祸福的控制权不在于自己,所以即使独处也能感到快乐,即使无所作为也能治理好。
圣人守护自己所拥有的,不去追求没有得到的东西。追求自己没有的,就会失去已有的;修养自己所拥有的,就会得到想要的。
所以用兵的人,先要做到不可被战胜,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治理国家的人,先要做到不可被夺取,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夺取。
舜在历山修养自己,四海之内都受到了教化;文王在歧周修养自己,天下风气都得到了改变。如果舜只追求天下之利而忘记修养自己的道德,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保全,又怎么可能拥有土地呢!
所以治理国家不在于不乱,而是那些致力于治理的人必须时刻警惕;行为不在于没有错误,而是那些急于求名的人必然会遇到危险。
福气没有比没有灾祸更大的,利益没有比不丧失更美的。
行动的结果要么是损害要么是增益,要么是成功要么是失败,要么是有利要么是有害,这些都是危险的,遵循道的人是危险的。
所以秦国虽然战胜了戎人,却在骰之战中败北;楚国虽然战胜了诸夏,却在柏莒之战中败北。
因此,追求利益不能被鼓励,而避开危害是可以的。所以经常没有灾祸,不经常有福气;经常没有罪过,不经常有功绩。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预设,来的人不迎接,去的人不送行,无论别人如何变动,他都能独立于中央。
所以即使身处众多邪曲之中也不失其正直,天下都流离失所,他却始终不离自己的原则。
因此,不刻意行善,也不刻意避免丑恶,遵循自然之道;不刻意开始,也不专断己见,遵循自然的规律。不预先策划,不放弃时机。
与天约定,不追求得到,也不拒绝福气,顺应天的法则。不追求没有的东西,也不失去已有的,内无灾祸,外无福气,灾祸和福气都不会发生,怎么会有人来侵害呢?
行善就观察,做恶就议论;观察就会得到尊重,议论就会带来麻烦。
道术不能用来追求名声,而可以用来退而修身;不能用来获得利益,而可以用来避开危害。
圣人不会因为行为而追求名声,也不会因为智慧而希望被赞誉。遵循自然,自己不参与其中。
思虑再多,行为再好,事情再符合道,做的人可能会有不成功,求的人可能会有得不到。
人有穷尽,而道却无所不通,与道争斗就会带来凶险。
所以《诗经》中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智慧而不行动,与没有智慧的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有能力而不做事,与没有能力的人有相同的德行。
有智慧的人,等到他行动了才会意识到他的活动;有力量的人,等到他施展了才会意识到他的作为。
有智慧却像没有智慧一样,有能力却像没有能力一样,这是道的正道,所以功盖天下,却不展示自己的美德;恩泽及后世,却不留名。
名和道不能同时显明,人追求名声,道就不会被使用;道胜过人,名声就会消失,道与人争长。
宣扬人的,就是阻碍道的人。人宣扬道,道就会消失,那么危险就不远了。
所以,世上有盛名的时候,衰败的日子也就快到了。想要占有名声的人必须行善。想要行善的人必须生事,事情一多就会放弃公义而追求私利,财富一多就会任由自己的欲望。
想要因为行善而得到赞誉,因为品质而建立名声,那么治理国家就不会完善,事情也不会适时处理。
治理国家不完善,就会多受责备;事情不适时处理,就不会有功绩。
责备多功绩少,无法弥补,就会胡乱行动去追求应该得到的,胡乱行事去追求合适的结果。
功绩一旦成就,不足以改变责备;事情一旦失败,不足以损害自身。
所以,重视行善就像重视做恶一样,接近于道了。
天下并非没有诚信的人,面对财物分配时一定会用抽签来决定,认为有私心的人对于公平,不如没有私心的人。
天下并非没有廉洁的人,然而守护重要财宝的人一定会关上门来,封好印章,认为有欲望的人对于廉洁,不如没有欲望的人。
人们因为自己的缺点而怨恨他人,镜子反映出自己的丑陋就认为镜子好。
人能够接触事物而不沾染自己,就可以避免麻烦。
公孙龙擅长辞令却换取了名声,邓析巧辩却扰乱了法度,苏秦善于游说却导致国家灭亡。
遵循他们的道路,善行就不会被彰显,修养他们的道理,技巧就不会有名。
用技巧斗争的人,开始时可能胜利,但最终常常失败;用智慧治理国家的人,开始时可能治理得好,但最终常常导致混乱。
让水流向低处,谁都能治理;让水逆流而上,不是技巧就能做到的。
文采过多会掩盖实质,邪巧会堵塞正道。
德行可以自己修养,却不能让别人变得残暴;道可以自己治理,却不能让别人变得混乱。
即使有圣贤的智慧,如果没有遇到暴乱的时代,可以保全自身,却不能成为霸王。
商汤、周武王的王位,是因为遇到了桀、纣的暴政而得到的。桀、纣并不是因为商汤、周武王的贤能而变得残暴,而是商汤、周武王遭遇了桀、纣的暴政而得到了王位。
所以,即使是贤明的君王,也必须等待时机。
时机,是能够遇到并把握住的时代,不是凭借智慧和才能就能求得的。
君子修养自己的德行,却使善行不为人知,布施恩惠却使仁爱不为人知,所以士人行善却不知道善的来源,民众得到利益却不知道利的来源。
因此,无为而自治。
善行被彰显,士人就会争夺名声;利益有根源,民众就会争夺功利。这两种争夺产生,即使是贤者也无法治理。
所以圣人隐藏自己的善行,使自己的仁爱不被知晓。
在外交中寻求援助,处理大事以实现安宁,不因内部治理而等待时机。
所有求助于人的人,不是因为宝物和金钱,而是因为谦卑的言辞。用玉帛作为礼物,财富耗尽而欲望却得不到满足;谦卑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才能使人信服而不结交;约束和誓言一旦达成,反目成仇的日子就没有了;即使割让国家的微不足道的财物去侍奉他人,如果没有自持之道,也不足以保全自己。
如果真诚地放弃外交的策略,而谨慎地治理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增加积累,激励民众的勇气以加固城池,上下一心,君臣同心,共同守护国家,教育民众使其不离不弃,那么追求名声的人不会夸耀无罪,追求利益的人不会攻击难以战胜的敌人,这是保全自己的必经之路。
民众有共同的道路,有共同遵守的法律,为了义不能相互巩固,威严也不能相互保证,所以设立君王来统一民众。
君王掌握统一,国家才能治理;没有统一,国家就会混乱。君王之道,不是用来做的,而是用来无为的。
什么叫做无为?智者不以职位为事,勇者不以职位为暴,仁者不以职位为忧,这样就可以说是无为的了。
无为,就是达到了统一。统一是万物的根本,是无敌之道。
人的本性,年轻的时候放纵不羁,壮年时凶猛强大,老年时贪图利益。一个人的身体都经历了多次变化,更不用说国家多次改变法律,更换君王了!
人因为职位而通晓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下面的路径复杂得无法理清,所以君王失去统一就会混乱,比没有君王的时候还要严重。
所以《诗经》中说:‘不犯错误,不忘记,遵循旧有的法则。’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君王喜好智慧,就会违背时宜而任由自己的意愿,放弃常规而依赖思虑。天下的东西繁多而智慧浅薄,用浅薄的智慧去应对繁多的东西,没有谁能做到。
只依赖自己的智慧,失误必然很多。
所以喜好智慧,是穷途末路;喜好勇猛,就会轻视敌人而简化准备,自以为是而拒绝帮助。
一个人用尽全力去对抗强大的敌人,不依靠众多的人而只依赖自己的才能,必然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喜好勇猛,是危险的策略。
喜好施舍,就会没有固定的界限。上面的界限不确定,下面的期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征税赋,充实国库,就会与民众为敌。少征税赋,多给予,这种情况从未有过。
所以喜好施舍,是引起怨恨的道路。
仁、智、勇、力,是人的美好才能,却不足以治理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出,贤能不足以担任治理天下的重任,而道术是可以修养和明亮的。
圣人克服自己的私心,普通人克服自己的欲望。君子行为正直,小人行为邪恶。内心顺应本性,外部符合道义,遵循道理行动,不拘泥于物质的是正气。重视口味,沉溺于声色,因为喜怒而忽视后果的是邪气。邪气和正气相互伤害,欲望和本性相互侵害,不能同时存在。一个存在另一个就废弃,所以圣人减少欲望而专注于本性。
眼睛喜欢美色,耳朵喜欢声音,嘴巴喜欢美味,接触并享受它们。不知道利害和欲望,食物吃下去不使身体安宁,听到的声音不符合道义,看到的景象不便于本性。三个感官(眼耳口)相互争斗,以道义为准则的是心。割除痈疽虽然痛苦,喝毒药虽然苦涩,但是这样做是因为对身体有益。口渴了喝水虽然痛快,饿了吃饱虽然满足,但是不做这些是因为对本性有害。这四者,耳目鼻口不知道取用,心为之决定,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
由此看来,欲望是不可战胜的。凡是修养身心,节制睡眠和休息,适当饮食,调和喜怒,使身心得到平衡,使邪气不生,哪里像担心肿瘤和痈疽的发作,而提前做好准备呢!牛鼎中的水沸腾了,苍蝇蚊子不敢靠近,昆山的玉石虽然光彩夺目,灰尘污垢也不能沾染。圣人没有摒弃之心,心中没有丑恶,没有追求之美,美就不会失去。因此,不追求福利的人能够得到亲人,不追求恩德的人能够招待宾客,只有不追求的人才能得到。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心,所以被称为尊贵,而不是贤能;拥有大地的人,因为有常规而没有阴谋,所以被称为平和,而不是智慧。内部没有暴行以免百姓怨恨,外部没有贤行以免被诸侯忌恨,上下之间的礼节,继承而不离异,这就是所谓的隐藏无形。不是隐藏无形,谁能显现出来!三代所倡导的是顺应自然。
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为顺应水的本性;后稷播种谷物,是因为顺应土地的本性;汤、武平定暴乱,是因为顺应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却不能强取,霸王可以接受却不能强求。
在智慧上,人们会与他争论;在力量上,人们会与他争斗。没有使人失去智慧的人,只有使人不能运用智慧的人;没有使人失去力量的人,只有使人不能施展力量的人。这两者常常是长久可见的。所以君王贤明不被看到,诸侯不会防备;不贤明不被看到,百姓不会怨恨。百姓不怨恨,民用才能得到;诸侯不防备,天下的大势才能承接。
事情与众人相同,功绩与时代成就,圣人没有这些。所以老子说:‘老虎没有地方施展它的爪子,犀牛没有地方施展它的角。’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鼓声不会因为声音而消失,所以能发出声音;镜子不会因为形状而消失,所以能映出形状。金石有声音,不敲击不会发出响声;管箫有音乐,不吹奏就不会有声音。圣人内心隐藏,不先于事物而行动,事情来了才处理,事物到了才应对。
修饰外表会伤害内在,扶持情感会损害精神,看到表面会遮蔽本质。不能时刻不忘本质的人,一定会被本性所困扰;百步之内不忘自己的形象的人,一定会束缚自己的身体。所以羽毛美丽会伤害骨骼,枝叶美丽会伤害根茎。能够两者兼得的人,天下是没有的。
天有光明,不担心百姓的昏暗,百姓凿开窗户,自己取光。地有财富,不担心百姓的贫穷,百姓砍伐树木,自己取富。最高尚的道德像山岳一样,巍然不动,行者以此为准则。直率自己而满足万物,不要求回报,使用的人也不接受他的恩德,所以能够宁静而长久。
天地不给予,所以不夺取;日月没有恩德,所以没有怨恨。喜欢恩德的人必定有更多的怨恨,喜欢给予的人必定善于夺取。只有消除痕迹,顺应天地自然的人,才能掌握道理,而受到名望。
名望兴起,道义就流行,道义流行,人们就没有地位了。所以赞誉产生,诽谤随之而来,善行出现,怨恨随之而来。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前兆。只有不追求利益的人没有害处,只有不追求福分的人没有灾祸。
想要称霸的人,必定失去他的封地,称霸的人想要称王,必定丧失他的霸权。所以国家以保全为常,霸王只是寄居而已;身体以生存为常,富贵只是寄居而已,能够不因为天下伤害国家,不因为国家伤害自己的人,才能够托付天下。
不知道的人,放弃他已有的,追求他未得到的。苦心焦虑去追求弯曲的道路,所以福来了就高兴,祸来了就害怕,精神在谋略上劳累,智慧急速地处理事务;祸福刚刚萌生,终身不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让别人烦恼。
不高兴就忧虑,内心从未平静;坚持没有标准,被称为狂生。
君主喜好仁爱,那么没有功绩的人也会得到奖赏,有罪的人也会得到赦免;喜好刑罚,那么有功绩的人会被废弃,无罪的人会被处决。如果既不喜好仁爱也不喜好刑罚,那么处决而不被怨恨,施舍而不被感激,按照标准执行,身体不参与事务,就像天和地一样,为什么不能包容万物。
合而舍弃的是君王,制定而处决的是法律,民众已经受到处决,怨恨无处发泄,这就是所谓的道。道胜,那么人们就没有事情了。
圣人没有奇特的眼神,没有奇异的行为,眼睛不看,行为不观察,言语不议论,通达而不浮华,穷困而不恐惧,荣耀而不显赫,隐居而不穷困,与众不同而不见怪异,与众人相同,无法用言语描述,这就是所谓的通达。
升降揖让,奔跑飞翔,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本性所具有的,情感没有约束,行为是不得已的,不破坏结构,难道是故意为之吗!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不会故意悲伤;不得已而跳舞的人,不会故意华丽。
唱歌跳舞而不故意悲伤华丽的人,都是没有根心的人。擅长博弈的人不贪图利益,不担心不能取胜,平心静气,掌握平衡,行动遵循道理,即使不一定取胜,得到筹码也一定多。为什么?胜利在于技巧,不在于欲望。
奔跑的人不贪图最先,不担心最后,根据情况调整,驾驭心马,即使不能一定领先,马的力量一定会用尽。为什么?领先在于技巧,不在于欲望。
因此,消除欲望就能取胜,放弃智慧就能立道。多端的人会贫穷,多技艺的人会困顿,心不专一。
树木大了会伤害枝条,水大了会伤害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即使钻研也不会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一种方法,即使得到也不能保持。
《诗经》说:‘善良的人,君子的举止是一致的。举止一致,心就像结一样。’君子应该像结一样,保持一致。
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用来治理天下。周公在前面摇动不收,钟鼓悬挂不解,用来辅助成王,使天下安定。普通人即使百般晦涩,也坚守一个原则,不满足于安逸,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一个人同时听取天下的事情,一天时间有余而治理不足,是因为有人帮助。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就像尸体,守官的人就像祝宰。尸体虽然能够剥狗烧猪,但不去做,因为不能无亏;俎豆的排列,黍稷的先后,虽然知道但不教导,因为不能伤害。
不能祝的人不能做祝,不影响做尸体;不能驾驭的人不能做仆人,不影响做助手。所以地位越尊贵,身体越安逸,身体越大,事务越少。就像弹琴,小弦虽然紧张,大弦一定放松。
无为是道的本质;执后是道的形态。无为制约有为,这是策略;执后制约先发,这是计谋。运用策略则强大,审慎计谋则安宁。现在给人卞氏的壁,还没有接受的人,是因为先;寻求并得到它,即使有人怨恨也不反抗的人,是因为后。
三个人同住一室,其中两人争吵,争吵者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能相互倾听,即使一个人很愚蠢,也必须由他来决定,这不是因为智慧,而是不争。
两人争斗,一方胜利在旁边,帮助一方就能取胜,救助一方就能免于灾难,争斗者虽然强大,但必须制约胜利的一方,这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不争。
由此看来,后发制人,静胜于躁,这是计谋。背离正道,抛弃计谋,只求偶然的相遇,改变常规,容易导致错误,以知其要害,遮掩错误,过分则自以为是,适中则以为合适,暗中行险,终身不悔:这就是狂妄。
有灾祸则忧虑,有幸福则得意,有过错则后悔,有功绩则骄傲,却不知道反省:这就是狂人。
圆的符合圆规,方的符合矩尺,行走成为兽,静止成为文,可以治理少数人,但不能治理大众。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理家庭,但不能治理国家,洗涤杯子而食,洗涤酒杯而饮,洗涤后再馈赠,可以养家,但不能宴请三军。不改变规则不能治理大事,不简化不能团结大众。大乐必须简单,大礼必须简约。简单所以能顺应自然,简约所以能顺应大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无不系统,所以能成为帝王。
心中有忧虑的人,坐在筐床和软席上也不能安宁,吃菰米饭和吃粗粮牛也不觉得香甜,弹琴瑟听音乐也不觉得快乐。忧虑解除,然后吃饭香甜,睡觉安宁,安居乐业。
由此看来,生有快乐的方式,死有悲伤的方式。现在追求那些不能带来快乐的事物,却以伤害带来快乐的事物,所以即使富有天下,尊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成为悲伤的人。
人的本性,喜欢安逸而厌恶忧虑,喜欢舒适而厌恶劳苦。内心常常没有欲望,可以说是安逸;身体常常没有事务,可以说是舒适。在安逸中修养心灵,在舒适中放松身体,等待天命,内心自得其乐,不急于外界,即使天下再大,也不足以改变这一点。日月虽小,却无益于志向,所以即使地位低如高贵,贫穷如富有。
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谦,大勇不骄,这五者不废弃,就能接近方圆。
军队命令太多就会混乱,酒宴上规矩太多就会争斗。混乱会导致溃败,争斗会导致背叛。所以开始于都市的,常常比乡村大;开始于快乐的,常常比悲伤的大;开始简单的事物,其最终本质必定和谐。
现在有美酒佳肴来宴请,卑躬屈膝,言辞委婉地接待,想要和睦相处,却在争夺酒杯之间反而产生争斗,争斗后相互伤害,三族结怨,反而得到了他们所憎恨的,这就是酒的失败。《诗经》的失误在于偏离正道,音乐的失误在于缺少讽刺,礼仪的失误在于过于繁琐。徵音并非没有羽声,羽音并非没有徵声。五音无不有声音,而以徵羽定名的,是因为它们是胜利者。所以仁义智勇,是圣人具备的,然而都立有一个名字,是因为它们是重要的。阳气起于东北,终止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终止于东北。阴阳的开始,都是调和相似的,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有的热如焦沙,有的寒如凝水,所以圣人谨慎地积累。
水从山流出而流入海,谷物在野外生长而储藏在仓库,看到开始就知道结束。席子上的先放的是野菜,酒杯中的先放的是清酒,先煮的是鱼,先做的是黍羹,这些都是不快于耳目的,不适宜于口腹的,但先王却重视它们,先重视根本而后重视末节。圣人接物,千变万化,必有不变而顺应变化的人。寒与暖相反,大寒时大地结冰,火不会减弱其热;大热时石头融化,金子流淌,寒暑的变化,对自己没有增减,这是自然的本质。
圣人常常后发而不先发,常常顺应而不主动;不主动前进,不后退退让;随时三年,时机过去我先;过去三年,时机在我后;不去也不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只与有德者相合。有道的人,不失时机地帮助人;无道的人,失去时机而夺取人。正直自己,等待天命,时机到来不可迎而反;要遮掩错误,寻求和谐,时机过去不可追而援。所以不说我没有作为而天下远离,不说我不想要而天下不至。古代存留自己的人,乐其德而忘其贱,所以名声不动其志;乐其道而忘其贫,所以利益不动其心。名利充满天下,不足以概括其志,所以廉洁而能快乐,宁静而能淡泊。所以那些身体治理好的人,可以谈论道。
自身以上至于荒野那么遥远;自死而天下无穷那么浩瀚,以有限的生命,忧虑天下的混乱,就像忧虑河水之少,哭泣而增加它一样。龟活三千岁,但浮游不过三天,以浮游为龟忧虑养生之具,人一定会嘲笑他。所以不忧虑天下的混乱,而乐于自己身体治理好的人,可以谈论道。
君子行善不能保证福必来,不做坏事,也不能保证祸不会到来。福的到来,不是他所求的,所以不夸耀他的功绩;祸的到来,不是他所引起的,所以不后悔他的行为。内心修养达到极致而横祸降临的人,都是天意,不是人为。所以内心常保持宁静,积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
因此知道天命的人不迷惑,明白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之主死后,葬其尸体于广野之中,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所以神制约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称之为太冲。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淮南子-诠言训-注解
太一:指宇宙的本原,是道家哲学中的最高概念,意味着无极之极,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
分物:指万物从无极的太一分化出来,形成了不同的种类。
真人:道家哲学中的理想人格,指那些能够顺应自然、不追求名利、内心平静的人。
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这句话表达了圣人的境界,即不追求名声,不作为谋略的存放地,不承担事务,不作为智慧的掌控者。
义列于德而见:指道德高尚的人,其行为自然体现了正义。
至论:指最高深、最精微的言论或道理。
通性之情:指了解并顺应自己的本性。
通命之情:指了解并顺应自己的命运。
物莫不足滑其调:指万物都不会影响自己的调性或和谐。
原天命:指探究天命,即宇宙的规律和命运。
治心术:指修养心性,使之平和。
理好憎:指分辨自己的喜好和厌恶。
适情性:指顺应自己的情感和本性。
括囊,无咎无誉:出自《易经》,意为不张扬自己的才能,不引起是非。
霸王者:指能够统一天下、建立霸业的君主。
得道以御者:指掌握了道的人能够统治。
去载:指去除不必要的负担。
反性:指回归自己的本性。
虚己以游于世:指以虚静的心态面对世界。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指放弃道德原则而依赖智慧的人必然陷入危险。
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指放弃规律而依赖才能的人必然陷入困境。
守其分,循其理:指遵守自己的本分,遵循自然的规律。
圣人:指道德高尚、智慧卓越的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和道德品质。
可非之行:指值得批评的行为。
修足誉之德:修养自己的美德,不求他人赞誉。
祸福:指灾祸和幸福,古代哲学中常用来比喻世间万物的变化。
制:控制,决定。
闲居而乐:在安静的环境中享受生活。
无为而治:指不采取主动干预,让事物自然发展。
守其所以有:保持自己所拥有的。
不可胜:不可战胜。
不可夺:不可夺取。
历山:地名,相传为古代圣贤舜的治理之地。
歧周:地名,相传为古代圣贤文王的治理之地。
趋天下之利:追求天下人的利益。
修己之道:修养自己的道德。
善:善良,好事。
丑:丑恶,坏事。
道术:指治国或行事的方法和原则。
劝:勉励,促进。
宁避害者:宁愿避免危害的人。
思虑:思考,考虑。
设储:储备,准备。
坛域:界限,范围。
豫谋:预先策划。
时:时机,时间。
尸名:追求名声。
探筹而定分: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分配。
有心者:有私心的人。
无心者:无私心的人。
关户而全封:关闭门户,严密封锁。
守重宝者:守护重要财宝的人。
举其疵:指出别人的缺点。
鉴见其丑:看到自己的丑恶。
兔于累:避免麻烦。
公孙龙:古代著名辩士。
邓析:古代著名辩士。
苏秦:古代著名纵横家。
阳:光明正大。
阴:阴暗,不光明正大。
文胜则质掩:文采过多则掩盖了实质。
邪巧则正塞之:邪巧的行为则会阻碍正义。
自修:自我修养。
暴:暴虐,残暴。
自治:自我治理。
圣贤之宝:圣贤的智慧。
霸王:指称霸一方的君主。
遇:遇到,遭遇。
暴乱之世:动荡不安的时代。
治未固于不乱:治理国家并不是因为国家不乱。
无常则乱:没有常道就会导致混乱。
一:统一,一致。
猖狂:放纵不羁。
暴强:凶暴强大。
好智:喜欢智慧。
倍时:超越时代。
任己:依赖自己。
数:指策略和计谋,这里指执后之制先的策略。
用虑:依靠思虑。
博:广大,丰富。
搪博:应付众多。
独任其智:单独依赖自己的智慧。
偩:骄傲自满。
辞助:拒绝帮助。
定分:确定分配。
望无止:欲望没有止境。
赋敛:征税。
实府库:充实国库。
与民为仇:与民对立。
少取多与:少征多予。
怨:怨恨。
来怨之道:招致怨恨的方法。
美才:优秀的人才。
治天下:治理国家。
道术之可修明:道术可以通过修养而变得明确。
众人:指普通大众,没有特殊才能或道德品质的人。
君子:指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行为端正,品德高尚。
小人:指品德低下、行为不端的人。
性:指人的本性,即天生的、自然的状态。
义:指道德规范和正义的原则。
滋味:指食物的美味。
声色:指音乐和视觉上的美。
喜怒:指人的情绪反应。
后患者:指未来的不幸或困难。
三官:指眼、耳、口三个感官。
心:指人的思考、判断和决策能力。
痤疽:指皮肤上的疮疖。
滇:通“玷”,指污点。
义制:指以道德和正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常术:指常规的方法或手段。
铃谋:指阴谋诡计。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指古代中国的历史时期。
智:指智慧,包括知识和判断力。
力:指力量,包括体力或影响力。
无屈奇之眼:指不炫耀自己的才能或智慧。
瑰异之行:指奇特或非凡的行为。
通而不华:指通达而不炫耀。
穷而不慑:指处于困境而不畏惧。
荣而不显:指显赫而不张扬。
隐而不穷:指隐居而不贫穷。
异而不见怪:指与众不同而不引起别人的非议。
大通:指极高的境界或智慧。
不得已:指不得不做,出于无奈。
术:指具体的技巧和方法,这里指无为制有为的技巧。
淑人君子:指品德高尚的人。
仪一:指行为一致,不偏离正道。
南风:指《南风歌》,一种古代的诗歌形式。
成王:指周成王,周朝的一位君主。
匹夫:指普通百姓。
百晦一守:指坚守正道,不为外界诱惑所动。
尸:指古代祭祀时扮演死者的人。
祝宰:指主持祭祀的官员。
俎豆:指古代祭祀用的器物。
黍稷:指古代祭祀用的谷物。
张琴:指弹奏琴。
小弦:指琴上较细的弦。
大弦:指琴上较粗的弦。
无为:指顺应自然,不刻意干预,不强迫事物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在道家哲学中,无为是道的体现,强调顺应自然规律。
道: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道无形无象,却又无所不在,是宇宙万物生成和变化的根本原则。
执后:指在行动上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不急于争先,而是等待时机。
卞氏之壁:指卞氏家族的宝物,这里比喻为珍贵的物品。
直:指正确、正义。
斗:指争斗、争辩。
赢:指成功、胜利。
狂:指行为荒谬,不遵循常理。
础:指基础,这里比喻为事物的根本。
矜:指自夸、骄傲。
员:指圆形。
规:指圆规,这里比喻为规则。
矩:指直角尺,这里比喻为准则。
兽:指动物,这里比喻为自然状态。
文:指文雅、有秩序。
萝菜:指蔬菜。
瓶瓯:指瓶子。
堤:指堤坝,这里比喻为界限。
量粟而春:指量取谷物进行春磨。
数米而炊:指数取米粒进行炊煮。
治家:指管理家庭。
飨三军:指宴请三军,即军队。
易:指简单、容易。
简:指简单、不复杂。
天:指自然、天意。
地:指坚实、稳重。
系统:指统一、协调。
帝:指帝王,这里比喻为最高统治者。
筐床:指竹制的床。
袄席:指粗布床单。
菰饭:指菰米做的饭。
刍牛:指草料喂养的牛。
琴瑟:指古琴和瑟,都是古代的弦乐器。
芋:指芋头。
恬:指平静、安宁。
悯:指忧虑、悲伤。
佚:指安逸、舒适。
劳:指劳累、辛苦。
天命:指天意、命运。
几乡方:指接近于方圆的标准。
降北:指失败、溃败。
约:指约定、规定。
辩:指争辩、辩论。
鄙:指边远的地方。
都:指都城,这里比喻为重要地位。
调:指和谐、协调。
美酒嘉肴:指美味的酒和食物。
卑体婉辞:指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款待。
盈爵:指酒杯中装满了酒。
《诗》:指《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徵:指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宫音。
羽:指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商音。
仁义智勇:指仁爱、正义、智慧和勇气,是儒家提倡的四种美德。
方:指正方形。
东北:指方位,相当于现代地理中的东北方向。
西南:指方位,相当于现代地理中的西南方向。
调适:指调和、适应。
侵:指侵犯、干扰。
焦沙:指干燥的沙土。
凝水:指结冰的水。
玄酒:指未过滤的酒。
沮:指阻止、阻碍。
先生:指先出现的人或事物。
泰羹:指用黍米做的羹。
先王:指古代的贤明君主。
未:指未加工的、原始的状态。
物:指事物、物品。
万乘之主:指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即古代的帝王。
广野:指广阔的田野。
明堂:指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场所。
太冲:指极端的平静和和谐,是道家追求的境界。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淮南子-诠言训-评注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此句开篇即点明了无为和执后是道的本质和形态。‘无为’即顺应自然,不强求,是道的核心;‘执后’则是指把握时机,后发制人,是道的应用。这两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的原则。
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此句进一步阐述了无为和执后的具体运用。‘无为制有为’即通过无为来引导有为,这是治理国家的艺术;‘执后之制先’则是指通过把握时机来制约先机,这是运用策略的数学。
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此句强调了无为和执后在不同情境下的重要性。在实施策略时,掌握技巧则能显得强大;在运用数学时,审慎则能带来安宁。
今与人卞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此句以‘卞氏之壁’为例,说明了先机和后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不同效果。未主动接受的人,看似处于先机,实则被动;而主动寻求并得到的人,虽然可能引起怨恨,但仍然能保持后机。
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此句通过三人同舍的例子,说明了在纷争中,不争的智慧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两人相斗,一赢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此句进一步说明了在争斗中,不争的力量往往能制服争斗。
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此句总结了前文,强调了后发制人和静胜躁的策略。
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瞎:此之谓狂。此句批判了那些违背常理、追求短暂利益的人,认为这是狂妄的表现。
有祸则础,有福则赢,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此句进一步说明了狂人的特点,即不知反悔,不知自我反省。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此句通过圆形和方形的比喻,说明了在治理国家时,要遵循规律,不能随意变动。
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此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明了治理国家和家庭的不同。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此句强调了治理国家要遵循简易的原则,并以此达到和谐统一。
心有忧者,筐床袄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芋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此句说明了内心的忧愁会影响生活的质量,只有解除了忧愁,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此句指出人生有喜有悲,而那些追求无法带来快乐的事物,即使富有和尊贵,也无法避免悲哀。
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此句阐述了人的本性,即追求恬静和安逸,并以此达到内心的满足。
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此句强调了大道的五个特点:无形、无亲、无声、不嗛、不矜,认为只有具备这五个特点,才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本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此句说明了过多命令和约束会导致混乱,而过多辩论则会引发争斗。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此句批评了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交应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以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此句通过音乐和道德的比喻,说明了仁义智勇是圣人所具备的特质。
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此句阐述了阴阳的运行规律,并指出圣人应谨慎行事。
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凛,见所始则知终矣。此句通过自然现象的例子,说明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此句说明了先王重视根本,不追求表面的奢华。
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面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诉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此句说明了圣人能顺应万物,不为外界变化所动。
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此段阐述了圣人的处世之道,即顺应天道,不先不后,不进不退。
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此段说明了古代圣人的境界,即乐道忘利,保持内心的平静。
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此段说明了身治者才能谈论道,并指出圣人关注天下大局。
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此段通过龟的例子,说明了圣人不应为小事而忧虑,而应关注大事。
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此段说明了君子应顺应天命,不为福祸所动。
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此段说明了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以及圣人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