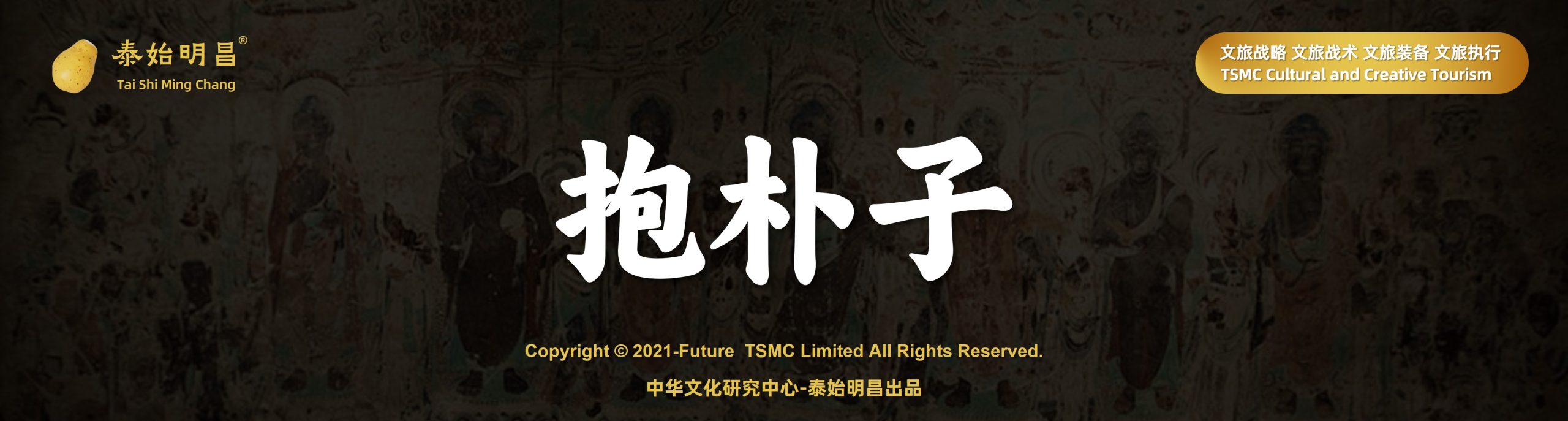作者: 葛洪(283年-363年),字君复,号抱朴子,晋代的道家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道家学术理论,还在于医学和炼丹术的研究。葛洪提出了许多关于长生不老、修身养性的理论,他的作品在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年代:成书于晋代(约365年)。
内容简要:《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集中讲述了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了长生不老的秘方和如何通过修炼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外篇》则多涉及炼丹术、医学、治病等实际操作。葛洪在书中不仅总结了自己关于炼丹和修道的经验,还提出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通过修身养性与练气,个人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甚至实现延年益寿。书中的医药学内容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医学与道家文化的珍贵遗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良规-原文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择木者,必有离罻之禽矣。
出身而不料时者,必有危辱之士矣。
时之得也,则飘乎犹应龙之览景云;时之失也,则荡然若巨鱼之枯崇陆。
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隐其身而有为也。
若乃高岩将霣,非细缕所缀;龙门沸腾,非掬壤所遏。
则不苟且於乾没,不投险於侥幸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摄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废昌邑,孙綝之退少帝,谓之舍道用权,以安社稷。
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载路;伊尹终於受戮,大雾三日;霍光几於及身,家亦寻灭,孙綝桑荫未移,首足异所。
皆笑音未绝,而号咷已及矣。
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争臣七人,无道可救。
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奸变,外引旧事以饰非,内包豺狼之祸心,由於伊霍,基斯乱也。
将来君子,宜深兹矣。
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
召王之谲,已见贬抑。
况乃退主,恶其可乎!此等皆计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
若夫阴谋始权,而贪人卖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
若有奸佞翼成骄乱,若桀之干辛推哆,纣之崇恶来,厉之党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
除君侧之众恶,流凶族於四裔,拥兵持疆,直道守法,严操柯斧,正色拱绳,明赏必罚,有犯无赦,官贤任能,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後行;君有违谬,据理正谏。
战战竞竞,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无患於下。
功成不处,乞骸告退,高选忠能,进以自代,不亦绰有余裕乎?何必夺至尊之玺绂,危所奉之见主哉!
夫君,天也,父也。
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
功盖世者不赏,威震主身危。
此徒战胜攻取,勋劳无二者,且犹鸟尽而弓弃,兔讫而犬烹。
况乎废退其君,而欲後主之爱己,是奚异夫为人子而举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养之,而云我能为伯瑜曾叁之孝,但吾亲不中奉事,故弃去之。
虽日享三牲,昏定晨省,岂能见怜信邪?
霍光之徒,虽当时增班进爵,赏赐无量,皆以计见崇,岂斯人之诚心哉?
夫纳弃妻而论前婿之恶,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犹不平之。
何者?重伤其类,自然情也。
故乐羊以安忍见疏,而秦西以过厚见亲。
而世人诚谓汤武为是,而伊霍为贤,此乃相劝为逆者也。
又见废之君,未必悉非也。
或辅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恶积,虑於为後患;及尚持势,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祸。
规定策之功,计在自利,未必为国也。
取威既重,杀生决口。
见废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归焉。
虽知其然,孰敢形言?无东牟朱虚以致其计,无南史董狐以证其罪,将来今日,谁又理之?独见者乃能追觉桀纣之恶不若是其恶,汤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
方策所载,莫不尊君卑臣,强干弱枝。
《春秋》之义,天不可雠。
大圣著经,资父事君。
民生在三,奉之如一。
而许废立之事,开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难以训矣。
俗儒沈沦鲍肆,困於诡辩,方论汤武为食马肝,以弹斯事者,为不知权之为变,贵於起善而不犯顺,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
而前代立言者,不析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锋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长世,远危之术。
虽策命暂隆,弘赏暴集,无异乎牺牛之被纹绣,渊鱼之爱莽麦,渴者之资口於云日之酒,饥者之取饱於郁肉漏脯也。
而属笔者皆共褒之,以为美谈,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使人悒而永慨者也。
或谏余以此言为伤圣人,必见讥贬。
余答曰:‘舜禹历试内外,然後受终文祖。虽有好伤,圣人者岂能伤哉!昔人严延年廷奏霍光为不道,於时上下肃然,无以折也。况吾为世之诫,无所指斥,何虑乎常言哉!’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良规-译文
抱朴子说:那些飞翔却不选择栖息树木的鸟,必定会被网捕;那些出仕却不考虑时机的士人,必定会遭遇危险和羞辱。时机得到时,就仿佛应龙欣赏云彩一样飘逸;时机失去时,就像巨大的鱼在枯竭的陆地上翻腾。因此智者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隐藏自己的身份有所作为。如果高山要倒塌,不是细小的绳子可以固定的;如果龙门的瀑布沸腾,不是捧土可以阻止的。所以不应该随便从事投机取巧的事情,也不应该冒险去侥幸成功。
抱朴子说:周公辅佐王位,伊尹罢黜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孙綝退位少帝,这些都被称为舍弃道德而使用权谋,来安定国家。然而周公被放逐,路上都是流言;伊尹最终被杀,大雾连续三天;霍光几乎丧命,家族也很快灭亡,孙綝的事情刚刚结束,他的首级和脚都被分开。这些事情刚刚被嘲笑,就已经有了悲惨的结局。
如果国家危难而不去维护,那么国君的辅佐还有什么用呢?有七个争臣,已经无法挽救无道的行为。导致王莽之流产生奸变,外面引用旧事来掩饰错误,内部怀有豺狼之心,从伊尹、霍光开始,就埋下了混乱的根源。未来的君子,应该深刻理解这一点。废立国君的事情,虽然表面上顺应人心,但实际上是大逆不道,不能让它延续。召王的行为已经被贬低。至于退位的主,怎能容忍!这些事情都是在事情成功之后才受到惩罚的。至于那些暗中策划夺取权力的人,如果贪婪的人卖了他,就会被灭族;而那些被封赏的人,也不少。
如果有奸佞之人助长骄乱,就像桀王时的干辛推哆,纣王时的崇恶来,厉王时的党羽一样,更换忠良的人,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清除国君身边的恶人,把凶恶的家族流放到边远地区,拥有军队和疆域,坚守正道和法纪,严肃执法,公正无私,有罪必罚,无人可以赦免,任用贤能,只与忠诚的人为伍,事情不专断,需要请示后才行动;如果国君有错误,要据理直言。战战兢兢,不忘敬畏,使国家永远安定,自己也不在下层担忧。功成不居,请求退休,选拔忠诚有才能的人来代替自己,不是绰绰有余吗?何必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呢!
国君,就像是天,就像是父。如果国君可以被废黜,那么天也可以改变,父也可以更换。功勋盖世的人不一定会得到奖赏,威震主的人身陷危险。这些仅仅是战胜攻取,没有其他功绩的人,尚且如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更不用说废黜国君,还想要后主对自己有爱,这和作为儿子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丢弃在山谷,而领养别人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说自己能够做到伯瑜、曾参那样的孝道,只是因为亲生父母没有好好对待,所以放弃了他们。即使每天享受丰盛的食物,早晚请安,又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信任呢?
霍光这些人,虽然当时增加了官职和爵位,赏赐无数,但都是因为权谋而被推崇,这难道是他们的诚心吗?把抛弃的妻子谈论前夫的恶行,买来的奴隶诋毁旧主人的暴行,普通人都会感到不平。为什么?因为伤害了自己的同类,这是自然的情感。所以乐羊因为忍辱负重而被疏远,而秦西因为过于宽容而被亲近。世人诚然认为汤武是正确的,而伊尹、霍光是贤明的,这其实是互相劝诱去做叛逆的事情。
被废黜的国君,未必全是错的。有的辅佐幼主,作威作福,罪大恶极,担心会成为后患;等到他们还掌握权力时,就趁机更换,以避免近期的祸患。他们规定策略的功绩,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未必是为了国家。一旦获得了威望,就会肆意杀戮,被废黜的国君失去了神器,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虽然知道是这样,但谁敢公开说出来?没有东牟朱虚来实施计谋,没有南史董狐来证明罪行,将来和现在,谁又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呢?只有那些有洞察力的人才能发现桀纣的恶行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恶,汤武的事情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美。
古代的文献记载,无不尊崇君主,贬低臣子,强调主干弱枝。春秋大义,天不可仇恨。伟大的圣人著书立说,教导人们尊敬父亲和君主。人民生活在天地之间,应该对君主和父亲一样尊敬。然而允许废立国君的事情,开启了不道德的先例,上下颠覆,难以教育。一些俗儒沉溺于诡辩,讨论汤武的事情时,认为吃马肝是为了弹劾这件事情的人,不知道权变的重要性,认为重要的是发起善行而不是违背常理和道义。
前代立言的人,没有用大道来分析,使得有这种想法的人站在了极端的位置,就像是登上险峻的山峰,这不是延年益寿、远离危险的方法。虽然策命暂时得到提升,奖赏突然集中,但这无异于给牛穿上花纹的绸缎,给鱼喂食麦子,口渴的人喝云雾中的酒,饥饿的人吃腐烂的肉和干肉。而那些写作的人却都赞美这些,把它们当作美谈,认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是权变,让人感到悲伤和感慨。
有人劝我,说这些话会伤害圣人,一定会受到批评。我回答说:‘舜和禹经过内外考验,然后继承了文祖。虽然有伤害,但圣人又怎么会伤害人呢?’过去有人严延年在朝廷上弹劾霍光为不道,当时上下肃然,无人可以反驳。何况我作为世人的警示,没有指名道姓,何必担心常人的言论呢?’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良规-注解
翔集:飞翔并栖息,指鸟类在空中飞翔并选择栖息地。
离罻:离开罗网,比喻脱离危险。
出身:出生,出身于某个家庭或社会阶层。
料时:考虑时机,把握时机。
危辱:危险和耻辱,指处于危险和受辱的境地。
应龙:古代神话中的龙,常用来比喻有才能的人。
览景云:观赏云彩,比喻时机。
巨鱼:大鱼,比喻强大的势力。
枯崇陆:干涸的陆地,比喻时机失去后的无望。
藏其器:隐藏自己的才能。
有待:等待时机。
隐其身:隐藏自己的身份。
有为:有所作为。
高岩将霣:高大的山岩即将崩塌。
细缕:细小的线,比喻微小的力量。
龙门沸腾:龙门的瀑布汹涌澎湃。
掬壤:捧起一把土,比喻微小的力量。
乾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侥幸:偶然得到成功或避免不幸。
摄王位:代理王位。
黜太甲:罢免太甲的职位。
废昌邑:废除昌邑王的王位。
退少帝:让少帝退位。
舍道用权:放弃道德原则而使用权谋。
安社稷:使国家安定。
放逐:流放。
狼跋:狼跳跃,比喻困难重重。
流言载路:谣言遍布道路,指谣言四起。
受戮:被杀。
大雾三日:大雾连续三天,比喻局势不明朗。
及身:涉及到自己。
家亦寻灭:家族也很快灭亡。
首足异所:头和脚在不同的地方,比喻死亡。
相:辅佐君主的大臣。
争臣: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
王莽:西汉末年的权臣,后篡位建立新朝。
奸变:奸诈的变化,指阴谋。
饰非:掩饰错误。
豺狼之祸心:像豺狼一样凶狠的心肠。
基斯乱也:这是乱的根源。
深兹:深刻理解。
废立:废黜或立新君主。
小顺大逆:小的顺从大的逆反。
长:助长,纵容。
召王:召唤王。
谲:欺诈。
退主:退位的君主。
恶:恶劣的行为。
计行事成:计划行事成功。
徐乃受殃:慢慢地才会受到灾祸。
阴谋始权:开始时是阴谋,后来成为权力。
赤族:全族被杀。
殄祀:灭绝祭祀。
翼成骄乱:助长骄横和混乱。
干辛推哆:比喻凶猛的人。
崇恶来:指恶人。
党:同党,指一伙人。
改置:更换。
忠良:忠诚善良的人。
除君侧之众恶: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
流凶族於四裔:将凶恶的族人流放到四方。
持疆:坚守边疆。
直道守法:坚持正义和遵守法律。
严操柯斧:严格执法。
正色拱绳:保持正直的态度。
明赏必罚:奖赏明显,惩罚必严。
有犯无赦:有罪必罚,绝不宽恕。
官贤任能:任用贤能的人。
唯忠是与:只与忠诚的人为伍。
事无专擅:事情不专权独断。
请而后行:请示后再行动。
违谬:错误的行为。
正谏:直言进谏。
战战竞竞:小心谨慎的样子。
恭敬:尊敬和谦恭。
社稷永安:国家永远安定。
乞骸告退:请求退休。
高选忠能:选拔忠诚有才能的人。
进以自代:推荐他们来代替自己。
绰有余裕:非常充足。
玺绂:皇帝的玉印和佩带。
见主:见到君主。
增班进爵:增加官职和爵位。
计见崇:因为计谋而受到推崇。
纳弃妻:接纳被抛弃的妻子。
论前婿之恶:评论前夫婿的恶行。
买仆虏:购买奴隶。
毁故主之暴:诋毁前主人的暴行。
重伤其类:严重伤害同类。
安忍:安于忍辱。
见疏:被疏远。
过厚:过分优待。
见亲:被亲近。
汤武:商汤和周武王,古代的贤君。
伊霍:伊尹和霍光,古代的权臣。
相劝为逆:相互劝诱做逆反的事情。
东牟朱虚:指古代的忠臣。
南史董狐:指古代的史官。
方策:古代的书籍。
尊君卑臣:尊敬君主,贬低臣子。
强干弱枝: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加强中央集权。
天不可雠:天是不可仇恨的。
资父事君:侍奉父亲和君主。
民生在三:人民生活在三个等级中。
奉之如一:对待他们一视同仁。
许废立之事:允许废立君主的事情。
不道之端:不道德的开端。
下陵上替:下级侵犯上级,上级被取代。
训:教训。
沈沦鲍肆:沉溺于酒色。
诡辩:狡辩。
食马肝:吃马肝,比喻不顾道德。
权之为变:权谋的变化。
起善而不犯顺:发起善行而不违背常理。
反理而叛义正:违反常理而背叛正义。
立剡锋之端:站在锋利的刀尖上。
登方崩之山:登上即将崩塌的山。
延年长世:延长寿命。
远危之术:远离危险的方法。
牺牛之被纹绣:祭祀用的牛被装饰。
渊鱼之爱莽麦:深渊中的鱼喜欢草。
渴者之资口於云日之酒:口渴的人把云和太阳当作酒。
饥者之取饱於郁肉漏脯:饥饿的人从肉和干粮中获取饱腹。
属笔者:写书的人。
褒:赞扬。
美谈:美好的谈论。
不容诛之罪:不可饶恕的罪行。
悒而永慨:感到悲伤和永远遗憾。
严延年:古代的忠臣。
廷奏:在朝廷上上奏。
不道:不道德的行为。
折:反驳。
世之诫:世人的教训。
无所指斥:没有指责。
常言:常规的话。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良规-评注
抱朴子以翔集不择木的禽鸟和出身不料时的士人作为比喻,警示人们应顺应时势,不可盲目行事。‘翔集而不择木者,必有离罻之禽矣’这句话,揭示了自然界中物竞天择的规律,也寓意了人应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否则将面临困境。
‘出身而不料时者,必有危辱之士矣’进一步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考虑时机,即使是出身显赫的人也可能遭遇危险和耻辱。
‘时之得也,则飘乎犹应龙之览景云;时之失也,则荡然若巨鱼之枯崇陆’通过对比应龙和巨鱼的境遇,生动地描绘了时机得与失带来的巨大差异。
‘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隐其身而有为也’提出了智者的处世之道,即在时机未到时隐藏自己的才华,等待时机成熟再施展抱负。
‘若乃高岩将霣,非细缕所缀;龙门沸腾,非掬壤所遏’用高岩和龙门的比喻,说明了伟大事业需要强大的基础和条件,不能轻率行事。
‘则不苟且於乾没,不投险於侥幸矣’是对前文的总结,强调不应为了短期利益而冒险行事。
‘周公之摄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废昌邑,孙綝之退少帝’列举了历史上几位权臣摄政或废立皇帝的例子,用以说明舍道用权的行为。
‘谓之舍道用权,以安社稷’指出这些行为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定,但实际上是违背道德和法制的。
‘皆笑音未绝,而号咷已及矣’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这些权臣最终的下场,警示人们权力的滥用必将导致灾难。
‘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争臣七人,无道可救’提出了对于国家危难时是否需要贤臣的建议,认为在无道的情况下,即使有贤臣也难以挽救。
‘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奸变,外引旧事以饰非,内包豺狼之祸心,由於伊霍,基斯乱也’批评了王莽等人利用权谋,导致国家动荡。
‘将来君子,宜深兹矣’呼吁未来的君子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指出废立皇帝虽然看似顺应人心,但实际上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应长期存在。
‘召王之谲,已见贬抑。况乃退主,恶其可乎!此等皆计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分析了历史上废立皇帝的案例,认为这些行为最终都会导致灾难。
‘若夫阴谋始权,而贪人卖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揭示了阴谋夺取权力的人最终会遭受灭顶之灾。
‘若有奸佞翼成骄乱,若桀之干辛推哆,纣之崇恶来,厉之党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提出了在出现奸佞之臣时,应该及时更换忠良的建议。
‘除君侧之众恶,流凶族於四裔,拥兵持疆,直道守法,严操柯斧,正色拱绳,明赏必罚,有犯无赦,官贤任能,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後行;君有违谬,据理正谏’详细阐述了如何治理国家,强调法制和道德的重要性。
‘战战竞竞,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无患於下’提出了治国者的道德要求,即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确保国家的安定。
‘功成不处,乞骸告退,高选忠能,进以自代,不亦绰有余裕乎?何必夺至尊之玺绂,危所奉之见主哉!’强调了功成身退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贪恋权力。
‘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指出君权至高无上,不可轻易废除。
‘功盖世者不赏,威震主身危。此徒战胜攻取,勋劳无二者,且犹鸟尽而弓弃,兔讫而犬烹’批评了那些只知攻城掠地,不知安邦定国的人。
‘况乎废退其君,而欲後主之爱己,是奚异夫为人子而举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养之,而云我能为伯瑜曾叁之孝,但吾亲不中奉事,故弃去之’用比喻的手法,揭示了废君自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虽日享三牲,昏定晨省,岂能见怜信邪?’指出即使表面上孝顺,但内心不诚,也无法得到他人的信任。
‘霍光之徒,虽当时增班进爵,赏赐无量,皆以计见崇,岂斯人之诚心哉?’批评了霍光等人利用权谋获得地位和财富。
‘夫纳弃妻而论前婿之恶,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犹不平之。何者?重伤其类,自然情也’用比喻的手法,说明了人们对于背叛和诽谤的不满。
‘故乐羊以安忍见疏,而秦西以过厚见亲。而世人诚谓汤武为是,而伊霍为贤,此乃相劝为逆者也’分析了汤武和伊霍的行为,认为汤武是正义的,而伊霍是背叛的。
‘又见废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辅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恶积,虑於为後患;及尚持势,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祸’分析了被废皇帝的情况,认为并非所有被废的皇帝都是罪有应得。
‘规定策之功,计在自利,未必为国也。取威既重,杀生决口。见废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归焉’指出被废皇帝的罪行往往被归咎于他们。
‘虽知其然,孰敢形言?无东牟朱虚以致其计,无南史董狐以证其罪,将来今日,谁又理之?’表达了对于历史真相的担忧。
‘独见者乃能追觉桀纣之恶不若是其恶,汤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认为只有有远见的人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
‘方策所载,莫不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春秋》之义,天不可雠。大圣著经,资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强调了君臣关系和孝道的重要性。
‘而许废立之事,开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难以训矣’批评了废立皇帝的行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俗儒沈沦鲍肆,困於诡辩,方论汤武为食马肝,以弹斯事者,为不知权之为变,贵於起善而不犯顺,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批评了那些沉迷于诡辩的儒者,认为他们不理解权变的本质。
‘而前代立言者,不析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锋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长世,远危之术’批评了前代立言者没有用正确的道理来分析问题,导致出现了错误的行为。
‘虽策命暂隆,弘赏暴集,无异乎牺牛之被纹绣,渊鱼之爱莽麦,渴者之资口於云日之酒,饥者之取饱於郁肉漏脯也’用比喻的手法,说明了那些表面上的奖励和荣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而属笔者皆共褒之,以为美谈,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使人悒而永慨者也’批评了那些盲目赞美这些行为的人,认为他们是不知变通和缺乏判断力的。
‘或谏余以此言为伤圣人,必见讥贬。余答曰:“舜禹历试内外,然後受终文祖。虽有好伤,圣人者岂能伤哉!昔人严延年廷奏霍光为不道,於时上下肃然,无以折也。况吾为世之诫,无所指斥,何虑乎常言哉!”’表达了作者对于自己观点的坚定,认为自己的言论是为了警示世人,而非伤害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