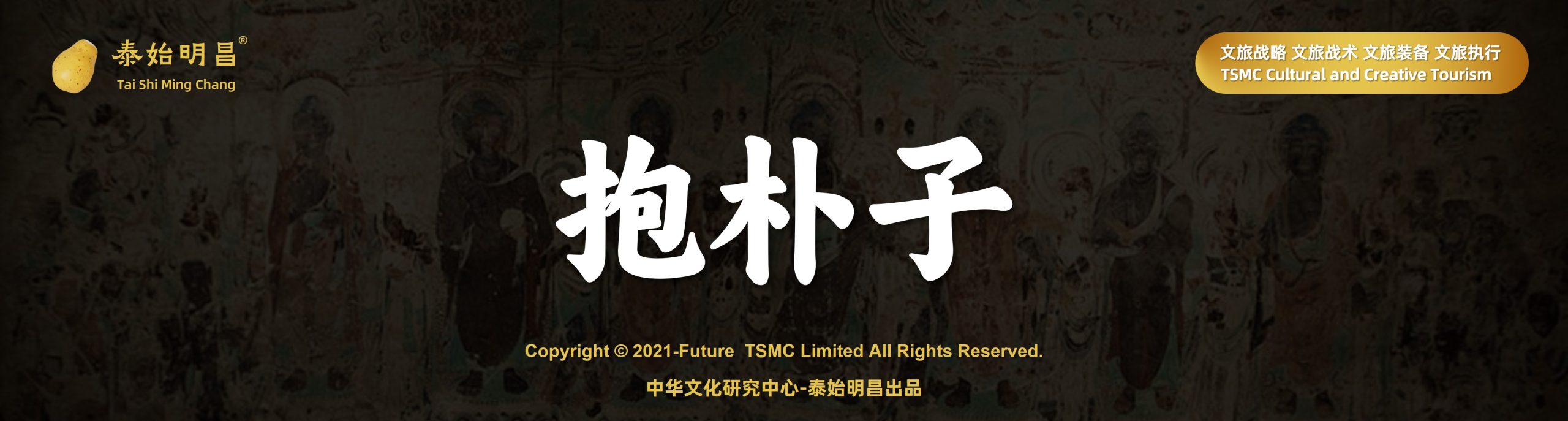作者: 葛洪(283年-363年),字君复,号抱朴子,晋代的道家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道家学术理论,还在于医学和炼丹术的研究。葛洪提出了许多关于长生不老、修身养性的理论,他的作品在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年代:成书于晋代(约365年)。
内容简要:《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集中讲述了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了长生不老的秘方和如何通过修炼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外篇》则多涉及炼丹术、医学、治病等实际操作。葛洪在书中不仅总结了自己关于炼丹和修道的经验,还提出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通过修身养性与练气,个人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甚至实现延年益寿。书中的医药学内容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医学与道家文化的珍贵遗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用刑-原文
抱朴子曰: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
或云:“明後御世,风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
余乃论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无悛,非刑不止。刑为仁佐,於是可知也。
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纳,含景内视,熊经鸟伸者,长生之术也。然艰而且迟,为者鲜成,能得之者,万而一焉。病笃痛甚,身困命危,则不得不攻之以针石,治之以毒烈。若废和鹊之方,而慕松乔之道,则死者众矣。
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
以杀止杀,岂乐之哉!
“八卦之作,穷理尽性,明罚用狱,著於《噬嗑》;系以徽纆,存乎《习坎》。然用刑其来尚矣。
逮於轩辕,圣德尤高,而躬亲征伐,至於百战,僵尸涿鹿,流血阪泉,犹不能使时无叛逆,载戢干戈。
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窜殛放流,天下乃服。
汉文玄默,比隆成康,犹断四百,鞭死者多。
夫匠石不舍绳墨,故无不直之木。
明主不废戮罚,故无陵迟之政也。
盖天地之道,不能纯仁,故青阳阐陶育之和,素秋厉肃杀之威,融风扇则枯瘁摅藻,白露凝则繁英凋零。
是以品物阜焉,岁功成焉。
温而无寒,则蠕动不蛰,根植冬荣。
宽而无严,则奸宄并作,利器长守。
故明赏以存正,必罚以闲邪。
劝沮之器,莫此之要。
观民设教,济其宽猛,使懦不可狎,刚不伤恩。
五刑之罪,至於三千,是绳不可曲也;
司寇行刑,君为不举,是法不可废也。
绳曲,则奸回萌矣;
法废,则祸乱滋矣。
亡国非无令也,患於令烦而不行;
败军非无禁也,患於禁设而不止。
故众慝弥蔓,而下黩其上。
夫赏贵当功而不必重,罚贵得得罪而不必酷也。
鞭朴废於家,则僮仆怠惰;
征伐息於国,则群下不虔。
爱待敬而不败,故制礼以崇之;
德须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肃之。
班倕不委规矩,故方圆不戾於物;
明君不释法度,故机诈不肆其巧。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
姬公友於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诛正卯,汉武之杀外甥,垂泪惜法,盖不获已也。
故诛一以振万,损少以成多,方之栉发,则所利者众;
比於割疽,则所全者大。
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以救弊也。
六军如林,未必皆勇。
排锋陷火,人情所惮。
然恬颜以劝之,则投命者鲜;
断斩以威之,则莫不奋击。
故役欢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诱悦者,未若刑戮之齐。
是以安於感深谷而严其法,
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
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不犯,全民之术也。
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
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
若乃以轻刑禁重罪,以薄法卫厚利,
陈之滋章,而犯者弥多,
有似穿阱以当路,非仁人之用怀也。
善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
治亲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
必有罪而无赦。
若石石昔之割爱以灭亲,
晋文之忍情以斩颉。
故仁者,为政之脂粉;
刑者,御世之辔策;
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
肃恭少怠,则慢惰已至;
威严暂驰,则群邪生心。
当怒不怒,奸臣为虎;
当杀不杀,大贼乃发。
水久坏河,山起咫尺。
寻木千丈,始於毫末;
钻燧之火,勺水可灭;
鹄卵未孚,指掌可縻。
及其乘冲飚而燎巨野,
奋六羽以凌朝霞,
则虽智勇不能制也。
故明君治难於其易,
去恶於其微,
不伐善以长乱,
不操柯而犹豫焉。
然则刑之为物,国之神器,
君所自执,不可假人,
犹长剑不可倒捉,
巨鱼不可脱渊也。
乃崇替之所由,
安危之源本也。
田常之夺齐,
六卿之分晋,
赵高之弑秦,
王莽之篡汉,
履霜逮冰,由来渐矣。
或永叹於海滨,
或拊心乎望夷,
祸延宗祧,
作戒将来者,
由乎慕虚名於住古,
忘实祸於当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兴,
盖存叔世。
立人之道,唯仁与义。
我清静而民自正,
我无欲而民自朴,
烹鲜之戒,
不欲其烦。
宽以爱人则得众,
悦以使人则下附。
故孟子以体仁为安,
扬子云谓申韩为屠宰。
夫繁策急辔,
非造父之御;
严刑峻罚,
非三五之道。
故有虞手不指挥,
口不烦言,
恭己南面,
而治化雍熙矣。
宓生政以率俗,
弹琴咏诗,
身不下堂,
而渔者宵肃矣。
必能厚惠薄敛,
救乏擢滞,
举贤任才,
劝穑省用,
招携以礼,
怀远以德,
陶之以成均,
治之以庠序。
化上而兴善者,
必若靡草之逐惊风;
洗心而革面者,
必若清波之涤轻尘。
朝有德让之群後,
野无犯礼之轨躅。
圜土可以虚芜,
楚革可以永格,
何必赏罚可以为国乎!
抱朴子答曰:“《易》称“明罚敕法”,
《书》有“哀矜折狱”。
爵人於朝,
刑人於市,
有自来矣,
岂从叔世!
多仁则法不立,
威寡则下侵上。
夫法不立,
则庶事汩矣;
下侵上,
则逆节明矣。
至醇既浇於三代,
大朴又散於秦汉,
道衰於畴昔,
俗薄乎当今,
而欲结绳以整奸欺,
不言以化狡猾,
委辔策而乘奔马於险途,
舍柁橹而泛虚舟以凌波,
盘旋以逐走盗,
揖让以救灾火,
斩晁错以却七国,
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见其可也!
盖三皇步而五常骤,霸王以来,载驰载骛。
当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盗公行,髡钳不足以惩无耻,族诛不能以禁觊觎。
重目以广视,累耳以远听,抗烛以理滞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犹市朝有呼嗟之音,边鄙有不闻之枉。
作威作福者,或发乎瞻视之下;凶家害国者,或构乎萧墙之内。
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
所谓刻舟以摸遗剑,叁天而射五步,掼犀兕之甲,以涉不测之渊;扲却寒之裘,以御郁隆之暑,踵之解除,颐之搔背,其为愦愦,莫此之剧矣!
但当先令而后诛,得情而勿喜,使伯氏无怨于失邑,虞芮知耻而无讼耳。
若强暴掩容,操绳而不惮,诱于含垢,莫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异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指沧海于万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于长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祸,脱沦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
然而为政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木半瓦胾,无救朝饥者也。
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使鼠,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也。
若行其言,则当燔桎梏,堕囹圄,罢有司,灭刑书,铸干戈,平城池,散府库,毁符节,撤关梁,掊衡量。
胶离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泛然不系,反乎天牧;不训不营,相忘江湖。
朝廷阒而若无人,民则至死不往来。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
俗儒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
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后至者斩,毕力赏罚,誓有孥戮。
考其所为,未尽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玩文,人主苛虐,号令不出宇宙,礼乐征伐,不复由己。
群下力竞,还为长蛇。伐本塞源,毁冠裂冕。或沈之於汉,或流之一彘。
失柄之败,由于不严也。
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内;白起王翦之伦,攻取於外。
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邻,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龙变龙视,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
降及杪季,骄於得意,穷奢极泰。加之以威虐,筑城万里,离宫千余,锺鼓女乐,不徒而具。
骊山之役,太半之赋,闾左之戍,坑儒之酷,北击猃狁,南征百越,暴兵百万,动数十年。
天下有生离之哀,家户怀怨旷之叹。白骨成山,虚祭布野。
徐福出而重号口兆之雠,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
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岂由严刑?此为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
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伤,为治国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伪不作,凶邪改志。
若纲绝网紊,得罪於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犹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杀人,存乎能用之与不能用。
夫症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术者,难图老彭之寿也。
奸党实繁,而不严弹违之制者,未见其长世之福也。
但当简于张之徒,任以法理世;选赵陈之属,季以案劾。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尽诚於下,见不善则若鹰鹯之搏鸟雀,睹乱萌则若草雉田之芟芜秽。
庆赏不谬加,而诛戮不失罪,则太平之轨不足迪。
令而不犯,可庶几废刑致治,未敢谓然也。
或曰:‘然则刑罚果所以助教兴善,式曷轨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复与?’
抱朴子曰:‘曷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积祀七百。汉氏废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轻刑之名,内有杀人之实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则其下唯有徒谪鞭杖,或遇赦令,则身无损;且髡其更生之发,挝其方愈之创,殊不足以惩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则死罪之下无复中刑在其间,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谪鞭杖,是轻重不得适也。又犯罪者希而时有耳,至於杀之则恨重,而鞭之则恨轻,犯此者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见治也。
今若自非谋反大逆,恶於君亲,及军临敌犯军法者,及手杀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则亦足以惩示凶人。而刑者犹任坐役,能有所为,又不绝其生类之道,而终身残毁,百姓见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肃栗,以彰示将来,乃过於杀人。杀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众,不见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为摽戒也多。
昔魏世数议此事,诸硕儒达学,洽通殷理者,咸谓宜复肉刑,而意异者驳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为然。
直以二陲未宾,远人不能统至理者,卒闻中国刖人肢体,割人耳鼻,便当望风谓为酷虐,故且权停,以须四方之并耳。
通人扬子云亦以为肉刑宜复也。但废之来久矣,坐而论道者,未以为急耳。]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用刑-译文
抱朴子说:没有人不看重仁爱,但没有人能够完全实行仁爱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没有人不轻视刑罚,但没有人能够废除刑罚来整顿民众。有人说:“明智的君主统治世界,风向草就会倒伏。道德教化普及,社会风气醇厚,还需要刑罚做什么?”我对这番话进行了评论说:“道德教化,就像是礼服上的花纹;刑罚,就像是防御用的铠甲。如果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狡猾凶暴的人,就像是穿着礼服去抵挡利刃;在和平时期使用刑罚,就像是把铠甲放在朝廷上。所以,仁爱是养育万物的工具,刑罚是惩罚罪恶的手段。我想让万物受益,但有些人却想伤害它们,只有施加刑罚才能阻止罪恶。”
比如修炼玄胎呼吸,吐纳呼吸,内视含景,像熊一样伸展,像鸟一样展翅,这是长生不老的技艺。然而,这个过程既艰难又缓慢,能够成功的人寥寥无几。如果病重痛苦,身体虚弱,生命垂危,那就不得不使用针灸和药物治疗。如果废弃了扁鹊的医术,而追求赤松子和羡门子的长生之道,那么死去的人会更多。仁爱作为政治手段,并非不好。然而,百姓中有些人狡猾虚伪,追求利益而忘记道义。如果不使用威严来整治他们,用刑罚来纠正他们,远离尧舜时代的风气,那么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其祸害会非常严重。用杀戮来制止杀戮,难道是愿意看到的吗?
《易经》中说‘明确惩罚,严明法度’,《尚书》中有‘哀矜折狱’的说法。在朝廷上封赏,在市场上执行刑罚,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哪里是从叔世(指衰败的世代)开始的!仁爱过多,法律就无法建立;威严不足,就会导致下级侵犯上级。法律无法建立,那么各种事务就会混乱;下级侵犯上级,那么逆反的行为就会明显。到了三代时期,最纯厚的道德已经变得淡薄,到了秦汉时期,最朴实的风气已经散失,道德在古代已经衰落,风俗在当今已经轻薄,却想要用结绳的方法来整治奸诈欺诈的人,用言语来教化狡猾的人,放弃驾驭工具来驾驭狂奔的马在险峻的道路上,放弃舵桨来驾驭空船在波浪上,盘旋着追赶逃犯,用礼仪来救灾,用斩杀晁错来平息七国之乱,用舞动干戈来平定赤眉军,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能够厚施恩惠,减轻赋税,救济贫困,提拔有才能的人,鼓励农业生产,节约使用,用礼节来招揽远方的人,用德行来感化他们,用成均来教化他们,用庠序来治理他们。能够使上层社会兴起善良风气的人,一定能够像被惊风吹倒的草一样;能够洗心革面的人,一定能够像清波洗去轻尘一样。朝廷中有道德高尚的官员,民间没有违反礼节的行为。监狱可以空着,楚革可以永久地被遵守,何必一定要用赏罚来治理国家呢!
三皇时期,人们步行,五常逐渐形成。自从霸王以来,人们追求速度,不断奔跑。当社会风气败坏时,官吏欺骗民众,盗贼公然横行,割发示众不足以惩罚无耻之徒,灭族也不能禁止那些贪婪的人。人们用宽大的眼睛观察,用灵敏的耳朵倾听,用蜡烛处理复杂的事务,用焦心的努力来消除邪恶的根源,但市场上仍有叹息之声,边远地区也有冤屈不得伸张的情况。
那些作威作福的人,或许在他们的监视之下;那些危害国家的人,或许在他们的家中策划。而想要用太昊的方法来治理轻薄的习俗;用统一的声音来平息混乱,如果不明白因时制宜,明白损益的变化,那就如同刻舟求剑,用三只手射击五步远,用犀牛和犀牛的甲胄涉水,用抵御寒冷的皮衣来抵御炎热的夏天,跟在后面解除束缚,搔背按摩,这种混乱的情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但应该先下令然后惩罚,得到情况后不要高兴,让伯氏失去领地而不怨恨,让虞芮知道羞耻而不诉讼。如果强暴的人掩盖真相,拿起绳子而不害怕,被宽容所诱惑,不除去蔓延的恶行,依赖藏匿的疾病的大话,忘记了膏肓之急,这难道不像是口渴的人指着远方的沧海,而水已经到了身边,却还在森林中造船,怎能避免夸父的灾难,逃脱溺水之害呢!
世人轻视申韩的实用主义,赞美老庄的空谈。然而在治理国家时,不能忽视刑法,杀人者应该处死,伤人者应该赦免其罪,就像土木半瓦的肉不能解决朝饥一样。道家的言论虽然高深,但使用起来却会有弊端,它空洞而遥远,就像干将剑不能用来缝线,大象不能用来捕捉老鼠,金船不能越过阳侯的波浪,玉马不能驰骋千里。
如果按照他们的言论去做,那就应该烧毁镣铐,摧毁监狱,废除官员,废除刑法,铸剑为农具,平毁城池,解散府库,毁掉符节,拆除关卡,取消度量衡。封闭离朱的眼睛,堵塞子野的耳朵。自由自在,回归自然;不教导,不经营,相互遗忘在江湖之中。朝廷空空如也,好像没有人,民众则至死不往来。这些话可以讨论,但难以实行。
俗儒们只听说周朝因为仁爱而兴盛,秦国因为严酷而灭亡,但没有意识到周朝之所以得到它不完全是因为仁爱,秦国之所以失去它不完全是因为严酷。
以前周朝使用肉刑,剁脚割鼻。盟津的命令是后到者斩首,全力以赴的赏罚,誓言有孥戮。考察他们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仁爱。到了叔世,法律被忽视,文饰被玩弄,君主苛刻残暴,号令不出宇宙,礼乐征伐不再由自己决定。下面的人争相竞争,变成了长蛇。伐本塞源,毁冠裂冕。有的被流放到汉水,有的被流放到野猪之地。失去权力的失败,是因为不严。
秦朝初兴,官员能够得到人才。卫鞅、由余等人,在内实行法度;白起、王翦等人,在外攻城掠地。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取得威望,稳定霸业,吞噬四邻,吞并群雄,开拓土地,驱逐戎狄,龙变龙视,实际上依靠明确的赏罚,奠定了帝业。到了末世,他们骄傲自满,极尽奢侈,加上威严和残暴,建造万里长城,千座离宫,钟鼓女乐,不劳而获。骊山的工程,大量的赋税,左邻右舍的守卫,残酷地坑杀儒生,北击猃狁,南征百越,百万大军,动辄数十年。天下有生死离别的哀痛,家家户户怀着怨旷的叹息。白骨成山,空祭布野。徐福出而重号口兆之雠,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他们之所以灭亡,难道是因为严刑?这是秦朝因为严酷而得到它,不是因为严酷而失去它。
而且刑罚就像刀刃一样,巧者用来自卫,拙者用来自伤,治理国家而有道,辅之以刑罚,能够使邪恶不生,凶邪改变志向。如果法网破裂,得罪了天,用刑不当,危险必然迅速。这也就像水火一样,既能救人,也能杀人,关键在于能否正确使用。
如果不除去疾病,而不学习越人的方法,就难以达到老彭的寿命。奸党众多,而不严加弹劾,就看不到长久的福祉。应该挑选张之徒,任用法理治理世界;选择赵陈之属,季以案劾。明主在上留心,忠良在下尽诚,看到不善就像鹰鹯捕鸟,看到乱象就像草雉田除杂草。奖赏不误加,惩罚不失罪,那么太平的道路就不足为奇。命令而不犯,或许可以废除刑罚达到治理,但不敢肯定。
有人说:“那么刑罚确实是用来辅助教化兴起善行的,如何才能正确使用呢?至于古代的肉刑,是否可以恢复?”
抱朴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以前周朝使用肉刑,积祀七百年。汉朝废除它,年代不如。至于改为鞭打,大多数人都死了。表面上是有轻刑的名声,实际上是有杀人之实。至于犯罪,上面不足以处死,下面只有徒谪鞭打,或者遇到赦令,身体无损;而且剃掉他们的头发,打他们的伤口,这不足以惩罚次死之罪。现在废除肉刑,那么死罪以下不再有中刑,而次死罪不得不只限于徒谪鞭打,这是轻重不适宜的。而且犯罪的人很少,但经常有,至于杀之则恨重,鞭之则恨轻,犯这种罪的人很多。现在不使用肉刑,那么次死之罪,常常得不到治理。
现在如果除了谋反大逆,恶于君亲,以及临敌犯军法的人,以及手杀人的人,用肉刑代替死刑,那么也足以惩罚和警示凶人。而受刑的人仍然可以服役,能够有所作为,又不绝其生类之道,终身残毁,百姓看到,无不寒心,也足以使未犯者敬畏,以警示将来,这比杀人更严重。杀人固然严重,但罪犯三天后,行埋弃之,不知者众,不见者多。至于肉刑,作为警示的作用更多。
过去魏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许多博学多才的硕儒,通晓殷商之理的人,都认为应该恢复肉刑,而意见不同的人驳斥他们,都不合适。魏武帝也认为应该恢复。只是因为边疆未平定,远方的人不能理解这个道理,突然听说中国割人肢体,割人耳鼻,就会望风认为是残酷的,所以暂时停止,等待四方统一。通人扬子云也认为肉刑应该恢复。只是废除肉刑已经很久了,坐而论道的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用刑-注解
仁:在儒家思想中,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指爱人、同情心、仁慈和公正。它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也是治国的根本。
刑:刑是指刑罚,是法律的一部分,用于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在古代中国,刑罚种类繁多,包括死刑、肉刑、流刑等。
治:治理,指统治和管理国家或社会,使国家或社会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
德教:德教是指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人的品德,使之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它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黼黻:黼黻是古代的一种装饰华丽的礼服,这里比喻道德教化。
甲胄:甲胄是古代士兵的铠甲和头盔,这里比喻刑罚。
玄胎息:玄胎息是道家修炼的一种呼吸方法,指深呼吸、吐纳,以求长生。
和鹊:和鹊是指古代著名的医生扁鹊,这里比喻医术高明。
松乔:松乔是指古代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这里比喻道术高深。
羲农:羲农是指伏羲和神农,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这里比喻古代圣贤。
唐虞:唐虞是指唐尧和虞舜,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君主。
汉文:汉文是指汉文帝,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以仁政著称。
成康:成康是指汉成帝和汉康帝,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以德治著称。
匠石:匠石是指古代著名的木匠,这里比喻技艺高超。
绳墨:绳墨是古代木工用来画线的工具,这里比喻法度。
青阳:青阳是指春天,这里比喻生机勃勃的景象。
素秋:素秋是指秋天,这里比喻肃杀的景象。
融风扇:融风扇是指春风,这里比喻温暖的风。
白露:白露是指秋天的露水,这里比喻寒冷的天气。
黎庶:黎庶是指平民百姓。
威:威是指威严,这里指统治者对百姓的威慑力。
纠:纠是指纠正,这里指用刑罚来纠正百姓的行为。
羲农之风:羲农之风是指伏羲和神农时代的风俗,这里比喻古代的淳朴风气。
汉文玄默:汉文玄默是指汉文帝的治国理念,即清静无为。
成康比隆:成康比隆是指汉成帝和汉康帝的治国理念,即德治。
断四百:断四百是指汉文帝时期,一年内判处死刑的人数达到四百。
鞭死者多:鞭死者多是指汉文帝时期,鞭打至死的人数很多。
匠石不舍绳墨:匠石不舍绳墨是指匠石在制作木器时,始终不离开绳墨,比喻做事严谨。
明主不废戮罚:明主不废戮罚是指明智的君主不会废除刑罚。
陵迟之政:陵迟之政是指政治腐败,道德沦丧。
青阳阐陶育之和:青阳阐陶育之和是指春天展示出养育万物的和煦。
素秋厉肃杀之威:素秋厉肃杀之威是指秋天展示出严酷的肃杀之气。
融风扇则枯瘁摅藻:融风扇则枯瘁摅藻是指春风吹拂使枯萎的植物重新生长。
白露凝则繁英凋零:白露凝则繁英凋零是指秋露凝结使繁茂的花朵凋谢。
品物阜焉:品物阜焉是指万物丰盛。
岁功成焉:岁功成焉是指一年的农事收获。
宽而无严:宽而无严是指宽容而不严苛。
奸宄并作:奸宄并作是指邪恶行为同时发生。
利器长守:利器长守是指锋利的武器长期存在。
劝沮之器:劝沮之器是指鼓励和阻止的工具,这里指奖励和惩罚。
五刑之罪:五刑之罪是指古代的五种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
司寇行刑:司寇行刑是指司法官执行刑罚。
君为不举:君为不举是指君主不加以赦免。
绳曲:绳曲是指法度不严。
奸回萌:奸回萌是指邪恶行为滋生。
法废:法废是指法律被废除。
祸乱滋:祸乱滋是指祸乱增多。
众慝弥蔓:众慝弥蔓是指邪恶行为蔓延。
下黩其上:下黩其上是指下级贪污上级。
鞭朴:鞭朴是指用鞭子打。
僮仆:僮仆是指仆人。
征伐:征伐是指战争。
群下:群下是指下属。
不虔:不虔是指不敬。
爱待敬而不败:爱待敬而不败是指爱护和尊敬他人不会失败。
制礼以崇之:制礼以崇之是指制定礼制来推崇。
德须威而久立:德须威而久立是指道德需要威严才能长久存在。
班倕不委规矩:班倕不委规矩是指班倕不偏离规矩。
方圆不戾於物:方圆不戾於物是指方和圆不会与物相违背。
机诈不肆其巧:机诈不肆其巧是指阴谋诡计不会任意施展。
姬公:姬公是指周公,是周朝的著名政治家。
二叔:二叔是指周公的两个弟弟。
仲尼:仲尼是指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
正卯:正卯是指孔子的弟子。
外甥:外甥是指汉武帝的外甥。
灸刺:灸刺是指用艾灸和针刺治疗。
栉发:栉发是指梳理头发。
割疽:割疽是指割除恶疮。
六军:六军是指古代的六种军队。
排锋陷火:排锋陷火是指冲锋陷阵。
投命:投命是指拼命。
断斩:断斩是指斩首。
叱咤:叱咤是指大声呼喊。
诱悦:诱悦是指用甜言蜜语来诱导。
深谷:深谷是指深山中的山谷。
卫子:卫子是指卫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将领。
弃灰而峻其辟:弃灰而峻其辟是指禁止在道路上丢弃灰烬。
众慝:众慝是指众多的邪恶。
委规矩:委规矩是指放弃规矩。
唐虞其仁如天:唐虞其仁如天是指唐尧和虞舜的仁爱像天一样。
四罪:四罪是指古代的四种罪行。
姬公友於兄弟:姬公友於兄弟是指周公对兄弟的友好。
仲尼之诛正卯:仲尼之诛正卯是指孔子诛杀正卯。
汉武之杀外甥:汉武之杀外甥是指汉武帝杀外甥。
垂泪惜法:垂泪惜法是指流着泪不舍得执行法律。
慕虚名於住古:慕虚名於住古是指追求虚名。
忘实祸於当己:忘实祸於当己是指忘记自己面临的实际祸患。
刑辟:刑辟是指刑罚和法度。
叔世:指一个朝代的末期。
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是指立身处世的道理。
清静:清静是指清静无为。
自正:自正是指自然端正。
无欲:无欲是指没有欲望。
自朴:自朴是指自然纯朴。
烹鲜之戒:烹鲜之戒是指烹饪新鲜食物的禁忌。
繁策急辔:繁策急辔是指频繁鞭打和急促勒马。
造父:造父是指古代著名的驾车手。
三五之道:三五之道是指古代的治国之道。
有虞:有虞是指有虞氏,是古代的一个部族。
宓生:宓生是指宓子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
成均:成均是指古代的学校。
庠序:庠序是指古代的学校。
化上而兴善者:化上而兴善者是指教化上层社会的人并兴起善行。
靡草之逐惊风:靡草之逐惊风是指柔弱的小草被狂风吹得摇曳。
清波之涤轻尘:清波之涤轻尘是指清澈的波浪洗涤轻薄的尘埃。
圜土:圜土是指监狱。
楚革:楚革是指楚国的皮革,这里指楚国的法律。
刑辟之兴:刑辟之兴是指刑罚和法度的兴起。
明罚敕法:明罚敕法是指明确刑罚和法度。
哀矜折狱:哀矜折狱是指同情并审慎处理案件。
爵人於朝:爵人於朝是指在朝廷上授予爵位。
刑人於市:刑人於市是指在市场上执行刑罚。
庶事汩:庶事汩是指各种事务混乱。
逆节明:逆节明是指叛逆行为明显。
大朴:大朴是指纯朴的风气。
浇於三代:浇於三代是指被破坏于夏、商、周三代。
道衰於畴昔:道衰於畴昔是指道德衰落。
俗薄乎当今:俗薄乎当今是指风俗败坏。
结绳以整奸欺:结绳以整奸欺是指用结绳的方法来整治欺诈行为。
不言以化狡猾:不言以化狡猾是指不用言语来感化狡猾的人。
委辔策:委辔策是指放弃驾驭马车的辔绳和马鞭。
盘旋以逐走盗:盘旋以逐走盗是指绕圈子来追赶逃犯。
揖让以救灾火:揖让以救灾火是指用谦让的方式来救灾。
斩晁错以却七国:斩晁错以却七国是指斩杀晁错来平息七国的叛乱。
舞干戈以平赤眉:舞干戈以平赤眉是指用武力来平定赤眉军。
造父之御:造父之御是指造父驾驭马车的高超技艺。
有虞手不指挥:有虞手不指挥是指有虞氏不用手指挥。
口不烦言:口不烦言是指不用口说话。
恭己南面:恭己南面是指自己恭敬地坐在南面。
治化雍熙:治化雍熙是指治理得和谐昌盛。
弹琴咏诗:弹琴咏诗是指弹琴吟诗。
身不下堂:身不下堂是指不出门。
渔者宵肃:渔者宵肃是指渔民在夜间也很肃静。
厚惠薄敛:厚惠薄敛是指给予厚惠而收税少。
救乏擢滞:救乏擢滞是指救助贫困的人并提拔有才能的人。
举贤任才:举贤任才是指选拔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
劝穑省用:劝穑省用是指鼓励耕作并节约使用。
招携以礼:招携以礼是指用礼节来招揽人。
怀远以德:怀远以德是指用德行来感化远方的人。
陶之以成均:陶之以成均是指用教育来培养人。
治之以庠序:治之以庠序是指用学校来治理人。
洗心而革面:洗心而革面是指洗涤心灵并改变面貌。
圜土可以虚芜:圜土可以虚芜是指监狱可以闲置。
楚革可以永格:楚革可以永格是指楚国的法律可以永远规范人。
赏罚可以为国:赏罚可以为国是指赏罚可以治理国家。
三皇:指中国远古的三个传说中的帝王,即伏羲、神农、黄帝,代表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儒家认为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
霸王:指战国时期的强大诸侯国君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
载驰载骛:形容奔波忙碌,指统治者忙于征伐和治理。
弊:指弊端,社会风气败坏。
吏欺民巧:指官吏欺诈,百姓机巧。
寇盗公行:指盗贼横行。
髡钳:指剃光头发,颈戴铁圈,是古代的一种刑罚。
族诛:指诛灭全族,是古代的一种极刑。
重目以广视:指戴眼镜来扩大视野。
累耳以远听:指戴耳塞来听远处的声音。
抗烛以理滞事:指点灯照明来处理复杂的事务。
焦心以息奸源:指费尽心思来消除奸邪的根源。
太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即伏羲。
因革:指因袭和变革,指事物的发展变化。
损益:指减损和增益,指事物的调整。
刻舟求剑:比喻不懂事物已变而仍坚持老办法。
叁天而射五步:比喻目标不切实际,行动无的放矢。
掼犀兕之甲:指穿着犀牛和兕牛的皮甲,比喻穿着坚固。
涉不测之渊:指进入危险之地。
踵之解除:指跟随他人的步伐。
颐之搔背:指受人颐指气使。
伯氏:指古代的一个贵族,这里泛指有功之臣。
虞芮:指古代的两个国家,这里泛指有德之国。
申韩:指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子。
老庄:指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李耳)和庄子。
土木半瓦胾:指半人半兽的形象,比喻不伦不类。
干将:古代著名的铸剑师,这里指宝剑。
巨象不可使鼠:指大象不能用来捕捉老鼠,比喻人才用非所长。
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指金制的船不能航行在巨浪之上,比喻力量有限。
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指玉制的马不能奔跑千里,比喻物有所限。
燔桎梏:指焚烧刑具。
堕囹圄:指摧毁监狱。
罢有司:指废除官职。
灭刑书:指废除刑法。
铸干戈:指制造武器。
平城池:指削平城池。
散府库:指分发府库中的财物。
毁符节:指毁坏符节,指废除制度。
撤关梁:指拆除关卡。
掊衡量:指整顿度量衡。
胶离朱之目:指蒙蔽离朱的眼睛,离朱是古代著名的盲人,这里指蒙蔽视听。
塞子野之耳:指堵塞子野的耳朵,子野是古代著名的聋人,这里指蒙蔽视听。
泛然不系:指放任自流。
天牧:指自然的状态。
俗儒:指世俗的儒者,这里指那些只知书本不知实践的人。
周:指周朝,古代的一个朝代。
秦:指秦朝,古代的一个朝代。
肉刑:指古代的一种刑罚,包括斩首、劓鼻、刖足等。
盟津之令:指周武王在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发布的命令。
毕力赏罚:指竭尽全力奖赏和惩罚。
孥戮:指诛灭全族。
罔法玩文:指法律松弛,玩弄文字。
人主苛虐:指君主苛求和残暴。
礼乐征伐:指礼乐制度和军事征伐。
群下力竞:指臣子之间相互竞争。
长蛇:指势力庞大而不可收拾的集团。
伐本塞源:指从根本上铲除。
毁冠裂冕:指破坏冠冕,指破坏礼仪制度。
沈之於汉,或流之一彘:指流放或处死。
失柄之败:指失去权力导致的失败。
卫鞅:即商鞅,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
由余: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
白起: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
王翦: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
兼弱攻昧:指吞并弱小,攻击昏昧。
取威定霸:指取得威望,确立霸主地位。
吞噬四邻:指吞并周边国家。
咀嚼群雄:指吞并群雄。
拓地攘戎:指开拓土地,驱逐戎狄。
龙变龙视:指威严如龙,视如无人。
明赏必罚:指奖赏明确,惩罚坚决。
杪季:指末代。
骄於得意:指骄傲自满。
穷奢极泰:指极端奢侈。
锺鼓女乐:指音乐和歌舞女。
不徒而具:指不劳而获。
闾左之戍:指边防的戍卒。
坑儒之酷:指活埋儒者的残酷行为。
猃狁: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
百越:古代南方的一个民族。
暴兵百万:指大量的军队。
生离之哀:指生死离别之痛。
家户怀怨旷之叹:指家家户户都怀着怨恨和悲伤。
白骨成山,虚祭布野:指战场上尸骨成山,无人祭祀。
徐福: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士,据说他带领一批人东渡日本。
赵高:秦朝末年的权臣。
屯豺狼之党:指聚集了一群豺狼般的党羽。
十室九空:指十户人家九家空无一人,形容战乱后的荒凉。
慝伪:指邪恶和虚伪。
凶邪:指凶恶邪恶的人。
纲绝网紊:指法网混乱。
得罪於天:指触怒了天意。
症瘕:指疾病。
老彭:传说中的长寿者。
奸党:指奸邪的党羽。
严弹违之制:指严格弹劾违法的制度。
张之徒:指那些只知张牙舞爪的人。
赵陈之属:指那些忠诚的人。
季以案劾:指用法律来审查和弹劾。
鹰鹯:一种猛禽,比喻勇猛果断。
草雉田:指田野中的杂草。
芟芜秽:指割除杂草。
庆赏不谬加:指奖赏不错误。
诛戮不失罪:指惩罚不冤枉。
太平之轨:指通往太平的道路。
庶几:表示希望。
废刑致治:指废除刑罚以达到治理的目的。
抱朴子:指东晋时期的道士葛洪,著有《抱朴子》。
殷理:指殷商时期的理政之道。
二陲:指边疆。
远人:指边远地区的人。
中国:指中原地区。
权停:指暂时停止。
四方之并:指四方统一。
通人:指有见识的人。
扬子云:指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扬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用刑-评注
这段古文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从三皇五帝到霸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治理方式的演变。作者通过对比,揭示了社会弊病的根源,并对治理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盖三皇步而五常骤’一句,点明了三皇时期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而‘霸王以来,载驰载骛’则反映了从霸王时期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浮躁,治理难度加大。
‘吏欺民巧,寇盗公行’揭示了当时社会腐败的现象,‘髡钳不足以惩无耻,族诛不能以禁觊觎’则表明了当时法律手段的无力。
‘重目以广视,累耳以远听,抗烛以理滞事,焦心以息奸源’等句,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但也暴露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的弊端。
‘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指出,治理国家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不能墨守成规。
‘刻舟以摸遗剑,叁天而射五步,掼犀兕之甲,以涉不测之渊’等句,用生动的比喻,讽刺了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盲目和愚蠢。
‘但当先令而后诛,得情而勿喜’等句,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即先教育引导,后依法惩处。
‘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法家、道家思想的评价,作者认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更为实用。
‘若行其言,则当燔桎梏,堕囹圄,罢有司,灭刑书’等句,描绘了道家理想中的治理状态,即废除刑狱,实现天下太平。
‘俗儒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等句,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优劣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治国方面存在不足。
‘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等句,回顾了周朝时期的刑罚制度,作者认为肉刑在惩治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今若自非谋反大逆,恶於君亲,及军临敌犯军法者,及手杀人者,以肉刑代其死’等句,提出了恢复肉刑的建议,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