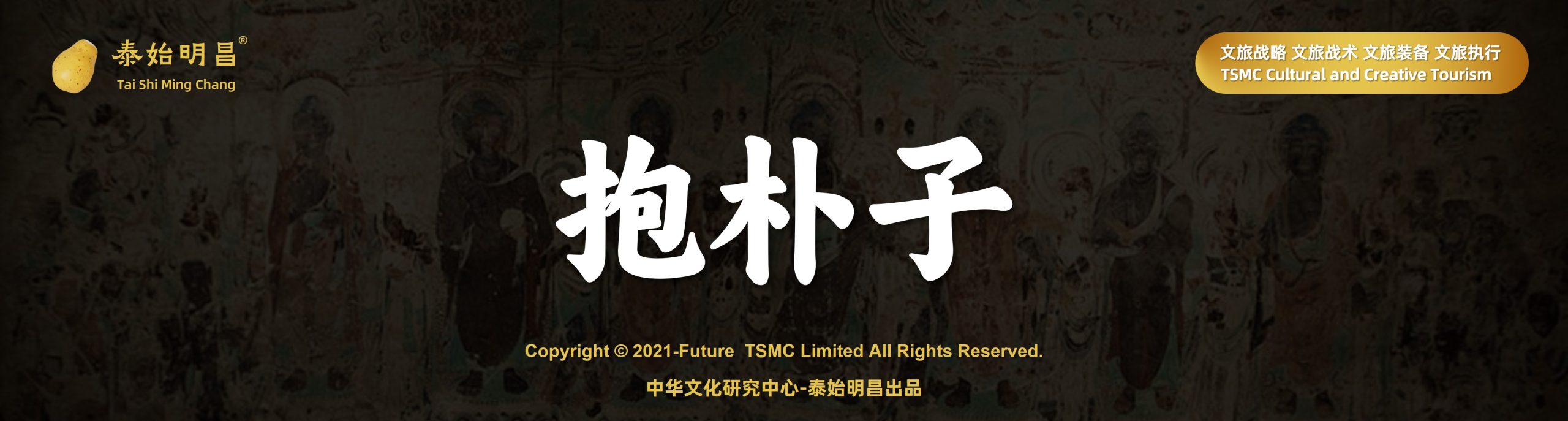作者: 葛洪(283年-363年),字君复,号抱朴子,晋代的道家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道家学术理论,还在于医学和炼丹术的研究。葛洪提出了许多关于长生不老、修身养性的理论,他的作品在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年代:成书于晋代(约365年)。
内容简要:《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集中讲述了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了长生不老的秘方和如何通过修炼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外篇》则多涉及炼丹术、医学、治病等实际操作。葛洪在书中不仅总结了自己关于炼丹和修道的经验,还提出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通过修身养性与练气,个人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甚至实现延年益寿。书中的医药学内容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医学与道家文化的珍贵遗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审举-原文
抱朴子曰:华霍所以能崇极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实赖股肱之良也。
虽有孙阳之手,而无骐骥之足,则不得致千里矣。
虽有稽古之才,而无宣力之佐,则莫缘凝庶绩矣。
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
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於丘园,驰翘车於岩薮,劳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
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
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
然夫贡举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简标颖拔萃之俊,而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
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卖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而见收。
夫铨衡不平,则轻重错谬;斗斛不正,则少多混乱;绳墨不陈,则曲直不分,准格倾侧,则滓杂实繁。
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立之朝廷,则乱剧於棼丝。
引用驽庸,以为党援,而望风向草偃,庶事之康,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弦不调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浊飞沉,沙汰臧否,严试对之法,峻贪夫之防哉!殄瘁攸阶,可勿畏乎?
古者诸侯贡士,适者谓之有功,有功者增班进爵;贡士不适者谓之有过,有过者黜位削地。
犹复不能令诗人谧大车素餐之刺,山林无伐檀罝兔之贤。
况举之无非才之罪,受之无负乘之患。
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复损乎?
夫孤立之翘秀,藏器以待贾;琐碌之轻薄,人事以邀速。
夫唯待价,故顿沦於穷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窍而腾跃矣。
盖鸟鸱屯飞,则鸳凤幽集;豺狼当路,则麒麟遐遁。
举善而教,则不仁者远矣;奸伪荣显,则英杰潜逝。
高概耻与阘茸为伍,清节羞入饕餮之贯。
举任并谬,则群贤括囊;群贤括囊,则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则小人道长;小人道长,则梼杌比肩。
颂声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
高干长材,恃能胜己,屈伸默语,听天任命,穷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堕多党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
逸伦之士,非礼不动,山峙渊渟,知之者希,驰逐之徒,蔽而毁之,故思贤之君,终不知奇才之所在,怀道之人,愿效力而莫从。
虽抱稷卨之器,资邈世之量,遂沈滞诣死,不得登叙也。
而有党有力者,纷然鳞萃,人乏官旷,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
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
台阁失选用於上,州郡轻贡举於下。
夫选用失於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於下,则秀孝不得贤矣。
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
於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
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
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
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
上为下效,君行臣甚。
故阿佞幸,独谈亲容。
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侩,各责其估。
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
又邪正不同,譬犹冰炭;恶直之人,憎於非党。
刀尺颠到者,则恐人之议己也;达不由道者,则患言论之不美也。
乃共构合虚诬,中伤清德,瑕累横生,莫敢救拔。
於是曾闵获商臣之谤,孔墨蒙盗跖之垢。
怀正居贞者,填笮乎泥泞之中,而狡猾巧伪者,轩翥乎虹霓之际矣。
而凡夫浅识,不辩邪正,谓守道者为陆沈,以履径者为知变。
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於德行,苦思於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
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
或曰:‘吾子论汉末贡举之事,诚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倾车之路,改有代之弦调,防法玩之或变,令濮上《巴人》,反安乐之正音,腠理之疾,无退走之滞患者,岂有方乎?士有风姿丰伟,雅望有余,而怀空抱虚,干植不足,以貌取之,则不必得贤,徐徐先试,则不可仓卒。将如之何?’
抱朴子答曰:‘知人则哲,上圣所难。今使牧守皆能审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终,诚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属托屈。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访以详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
‘又,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罪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转不得过故。若受赇而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与举者同罪。今试用此法,治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
又,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
如此,不廉之吏,必将化为夷齐矣。
若临官受取,金钱山积,发觉则自恤得了,免退则旬日复用者,曾史亦将变为盗跖矣。
如此,则虽贡士皆中,不辞於官长之不良。
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
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
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
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省夷吾之书,而明其有拨乱之干,视不害之文,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
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暗蔽也。
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之以对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要必愈於了不试也。
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
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
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
或曰:先生欲急贡举之法,但禁锢之罪,苛而且重,惧者甚众。
夫急辔繁策,伯乐所不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补之药,长於养体益寿,而不可以救日曷溺之急也。
务宽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
虎狼见逼,不挥戈奋剑,而弹琴咏诗,吾未见其身可保也。
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让盘旋,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
今与知欲卖策者论此,是与跖议捕盗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
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叁差而无检乎?
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
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
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
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
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
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於在昔也。
此乃见同於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
且夫君子犹爱人以礼,况为其恺悌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损化,其此之谓也。
今贡士无复试者,则必皆修饰驰逐,以竞虚名,谁肯复开卷受书哉?所谓饶之适足以败之者也。
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
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
学精不仕(疑有脱文)徇乎荣利者,万之一耳。
至於甯越倪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励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
向使非汉武之世,则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
今若取富贵之道,幸有易於学者,而复素无自然之好,岂肯复空自勤苦,执洒埽为诸生,远行寻师问道者乎?
兵兴之世,武贵文寝,俗人视儒士如仆虏,见经诰如芥壤者,何哉?
由於声名背乎此也。
夫不用譬犹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华夏矣。
今若遐迩一例,明考课试,则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
抱朴子曰:才学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
就令其人若桓灵之世,举吏不先以财货,便安台阁主者,则虽诸经兼本解,於问无不对,犹见诬枉,使不得过矣。
常追恨於时执事,不重为之防。
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
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
人事因缘於是绝。
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
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
违犯有罪无赦。
如此,属托之翼窒矣。
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
亦何耻於峻为斯制乎?
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矣。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
或有微言难晓,而小吏多顽,而使之决狱,无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
作官长不知法,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决其口笔者,愤愤不能知食法,与不食不问,不以付主者。
或以意断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
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审举-译文
抱朴子说:华山和霍山之所以能够达到极高的天空,是因为它们的基础非常深厚;唐尧和虞舜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辅佐之臣。即使有伯乐这样的眼光,如果没有千里马那样的脚力,也无法达到千里之外。即使有研究古代的才能,如果没有有力的助手,也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业。君主虽然聪明如同日月,神明未现,但是国家大事不能独自管理,琐碎之事不能亲自处理,必须借助他人的眼睛来远观,借助他人的耳朵来广听,确实需要官吏来协助,这样国家才能安康和繁荣。
因此,圣明的君主无不将招揽贤才放在心中,将选拔人才作为首要任务,把玉帛施舍给隐居的贤人,把骏马驰骋在山林之间,在寻找人才上辛勤努力,在任用人才上轻松自如,从高官显贵到普通百姓,讨论治国之道,没有人不担任自己的职责。
君主谦逊无为,而国家刑罚得以实施;而教化遍及四方,天下太平。设立官职,分配职责,就像建造房屋一样,如果有一物不能承受,就会导致房屋崩塌。然而,那些通过贡举的士人,按照四科标准,三事九列,都是自己出来的,必须选拔出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但是到了汉朝末年,桓帝和灵帝时期,政权离开了皇帝,掌握在奸臣手中,选拔人才不严,风气颓废,教化衰败,压制清德而推崇谄媚,贬低遵循道德的人而提拔财富多的人。势力竞争成为风俗,苟且偷生,有人献上自己的宝物,有人出售他人的书信,或者父兄显贵,通过拜访而获得任命;或者低头弯腰,积累恶习而被录用。
如果选拔不公平,就会导致轻重失序;如果斗升不正确,就会导致多少混乱;如果绳墨不摆放好,就会导致曲直不分,标准倾斜,就会导致杂质增多。用这些来治理人民,就会导致暴虐和贪婪,聚敛财富来弥补买官的费用;在朝廷上,就会混乱不堪。引用平庸之辈,作为党羽,希望风向草倒,希望事务顺利,这难道不是像悬着瓦砾而要求夜明珠一样,琴弦不调而要求清音吗?怎能不澄清混浊,淘汰优劣,严格考试制度,严厉防止贪婪呢?消除弊端,难道可以不害怕吗?
古代诸侯国贡举士人,合格者被称为有功,有功者增加官职和爵位;贡举不合格者被称为有过,有过者被剥夺官职和土地。即使如此,也不能让诗人停止对那些无功受禄者的讽刺,或者对那些在山林中捕兔的贤人的赞美。何况举荐的人没有犯下罪行,接受的人没有带来麻烦。衡量一旦失去标准,多少还能挽回吗?那些才华横溢的人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那些平庸的人通过人际关系追求快速成功。只有等待时机,才会陷入困境;只有追求快速,才会变得轻浮。
鸟儿聚集飞翔,凤凰就会隐居;豺狼横行,麒麟就会远去。举荐善良的人进行教化,不仁的人就会远离;奸诈伪善的人显赫,英雄豪杰就会隐退。高尚的人耻于与平庸之辈为伍,清白的人羞于进入贪婪者的行列。举荐和任命如果都是错误的,那么贤能的人就会退缩;贤能的人退缩,那么邪恶的人就会相互勾结;邪恶的人相互勾结,那么小人的道就会盛行;小人的道盛行,那么残暴的人就会并列。这就是为什么颂歌不出现,怨叹声不绝的原因。
高官显贵的人依仗自己的能力超过他人,他们的屈伸和言语都听天由命,他们的得失成败都交给自然,也难免会落在多党派之后,居于有权势者之下。超凡脱俗的人不按礼节行事,他们像山一样坚定,像水一样深沉,了解他们的人很少,追逐名利的人会掩盖和诋毁他们,所以思贤的君主最终也不知道奇才在哪里,怀有道德的人愿意效力却没有人跟随。即使有像稷和卨那样的大才,有超越时代的度量,也可能会沉沦而死去,无法得到重用。而有党派有权势的人,纷纷聚集,人缺乏官职,到达的人又很优秀,怎能不选拔他们来使用呢?
灵帝和献帝时期,宦官掌权,奸臣把持朝政,危害忠良。朝廷在上失去了选拔人才的能力,州郡在下轻视贡举。朝廷选拔人才不当,就会导致地方官吏不称职;州郡轻视贡举,就会导致优秀的人才不能被选拔。因此,当时的人说:‘举荐秀才,不知道书;考察孝廉,父亲分居。寒门出身的人清白如泥,高第的良将胆小如鸡。’又说:‘古人想要达到目标就勤奋读书,现在的人想要做官就避免经营生计。’这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强烈不满。
当时爵位可以买卖,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争相进入官场的人购买官职,就像市场上的商人一样。有财力的人可以不按规矩直接晋升,空手的人望而却步。财力多的人官位高,财力少的人职位低。因此,东园积累卖官的钱财,崔烈被嘲笑有铜臭味。上面的人效仿下面的人,君主的行为影响臣子。因此,阿谀奉承的人独占君主的宠爱。家乡议论君主,中正官吏和吏部官员都成为市场上的中介,各自负责评估。清贫的士人,有什么理由期望呢?既然如此,邪恶和正义不同,就像冰和炭一样;恨直的人讨厌非党派。刀尺颠倒的人,担心别人议论自己;不通过正当途径成功的人,担心别人的议论不美好。于是,他们共同编造虚假的事情,中伤清白的人,缺点和错误横生,没有人敢出来挽救。
于是曾子和闵子骞被商臣诽谤,孔子和墨子被盗跖一样的恶名所累。坚守正道的人陷入困境,而狡猾虚伪的人却高高在上。普通人缺乏见识,不能分辨邪正,认为坚守道德的人沉没无闻,认为走捷径的人懂得变化。俗世随风而动,随波逐流的人,怎能再回归道德,苦思学问呢?这都是因为放弃了道德的约束,追求快速的成功。这确实是汉朝衰败的原因,也是后代应该深刻反思的。
有人说:‘您谈论汉朝末年的贡举制度,确实指出了其弊端。现在如果想要避免过去的错误,避免倾覆的道路,改变后代的弦调,防止法律被忽视而发生变化,让濮上和巴人的音乐回归正音,消除疾病,没有退步的困扰,有什么方法吗?士人有风度翩翩,有高雅的声誉,但内心空虚,实际能力不足,以貌取人,不一定能得到贤才,慢慢尝试,也不可以仓促行事。应该怎么办呢?’
抱朴子回答说:‘了解人才是智慧的体现,即使是圣人也很难做到。现在让地方官吏都能在人才未使用之前审慎选拔,保持他们的本性直到最后,确实不容易。但只要大家摒弃私情,发挥聪明才智,不被利益所动,不屈服于他人的请求。想要举荐的人,必须深思熟虑,广泛咨询,修正名声并考察行为,比较同异以防止虚假。让亲戚称赞他们的孝顺友爱,让乡里归附他们的诚信正义。曾经担任小官职的人,有忠诚清廉的业绩,处理事务的能力,那么一件锦衣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巧妙,一只老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勇敢。’
再者,对于担任官职的人,如果他们犯了公罪,就按照法律来处理;如果是因为贪污腐败而犯罪,但罪行不足以判死刑的,那么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遇到赦免的情况下,都应当终身禁止他们担任官职,轻罪者禁锢二十年。这样一来,那些不廉洁的官员,必将变成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如果官员在任职期间接受贿赂,积累如山般的金钱,一旦被发现,就会自食恶果,如果免职了,十天后又可以重新任职,那么即使是像曾子、史鱼那样的人,也会变成盗跖一样的人。这样一来,即使是贡举考试及格的人,也不会因为官长的不良行为而辞官。
有人说:‘能说并不一定能做到,现在虽然通过了经学的对策考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处理政事的才能。’
抱朴子回答说:‘古代还用射箭来选拔人才,何况是经学呢?如果舍弃了经学,那就没有比这更贤明的选拔方法了。肥沃的草地不会长出杂草,大的鱼不会在小河里生长,至理名言不会出自庸人之口,高深的文章不会出自愚笨之人的笔下。因此,通过阅读《洪范》可以知道箕子有治理天下的才能,通过学习九术可以看到范蠡有治理国家的策略,阅读管夷吾的书籍,可以明白他有拨乱反正的才能,阅读不害的著作,可以看到他精通霸王之道。现在孝廉必须通过经学考试没有错误,秀才必须通过对策考试没有失误,这样也就不会因为无知而受到蒙蔽。优秀的将领通过考试选拔出勇敢的人,还要通过对策考试再次考验,何况是文人呢?即使不能保证一定能选拔出贤能之人,但总比完全不考试要好。
现在让天下所有应当参加贡举考试的人,都不敢不勤奋学习。仅这一条,对弘扬风教的长远利益来说,也不算小了。如果让全国都害怕因为推荐不当而受到损失,普通人停止了侥幸心理的追求,放弃了争名逐利的末节,回归到学问的根本,那么儒家思想将会兴盛,私人的财物必然逐渐消失,优秀的人才可以得到利用,各个官职都可以得到充实。
有人说:‘先生想要急切地推行贡举法,但是禁锢的罪行过于严苛且严重,害怕的人很多。急切地使用马鞭和鞭子,即使是伯乐也不这样做;严密地防范和严厉的法律,是德政所耻笑的。’
抱朴子说:‘那种能够补骨填肉的药,虽然长于养生延寿,但并不能用来救治日薄西山的急病。追求宽容和包容的政策,可以用来敦厚教化,但不适用于拯救衰败的风气。老虎和狼被逼迫时,不会挥舞武器和剑,而是弹琴吟诗,我未见这样的行为能保护自己。火势蔓延到屋内,不会奔跑浇水,而是行礼作揖,我未见这样的行为能扑灭火势。现在和那些想要通过考试来谋取私利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是和盗跖讨论如何抓捕盗贼一样。’
抱朴子说:‘现在天下统一,九州同风,王制政令,确实应该统一。即使是衡量小物件,也不应该让它们各有不同,何况是人才的选拔标准,怎么能随意差异而不加检验呢?江表虽然偏远,靠近海边,但是受到道德教化的影响,遵循礼教,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虽然过去暂时有所隔阂,不超过一百年,但儒学的事情也没有被废弃。只是因为地域狭小,所以人才的数量不能和中原地区一样均衡。至于那些德行和学问高深的人,像子游、仲任等人,也不比中原地区的人差。
过去吴地刚刚归附时,贡举考试因为不进行考试而受到批评。现在太平已经接近四十年了,还是不进行考试,这就是导致东南地区儒学衰落的原因。这就像是和异族一样,不是用来区分他们的方法。而且,君子还用礼来爱人,何况是他们的慈父慈母呢!法律有招致祸患的,命令有损害教化的,这就是所说的。
现在贡举考试没有复试,那么他们必然都会修饰自己的行为,追求虚名,谁还会愿意打开书本学习呢?这就是所谓的纵容反而足以败坏事情。
那些天生喜欢古代文化,心中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学习不是为了谋取俸禄,品味学问而忘记贫穷,就像高卿周生烈那样的人。学习精深而不追求名利的人,只有万分之一。至于像甯越、倪宽、黄霸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努力研究经典,并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因为困苦和劳累,想要通过经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汉武帝的时代,那么像朱买臣、严助那样的人,也不一定读书。现在如果想要通过读书来获得富贵,幸好有容易学习的方法,但如果本来就没有这种天生的喜好,怎么会愿意自己辛苦努力,拿着扫帚当学生,远行寻找老师学习呢?
在战争频繁的时代,武人受到重视,文人受到冷落,普通人把儒士看作仆人奴隶,把经书看作无足轻重的尘埃,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声名和这些不符。不学习就像是把帽子卖给夷人,把长须卖给华夏人。现在如果远近都一样,明确考试考核,那么一定会有人背负行囊千里迢迢去寻找老师和朋友,转而用送礼的钱财来购买书籍,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抱朴子说:有才能和学问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即使是在桓帝、灵帝的时代,选拔官员不首先看重财富,而是安心在台阁担任要职的人,即使对所有的经典都有深刻的理解,对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也可能会受到诬陷,使不能晋升。我常常对当时负责选拔的官员感到遗憾,他们不重视为这种情况做预防。
我认为新年即将到来的贡举考试,今年就可以让儒官和才士提前准备各种策略,计划足够使用。收集起来禁止他们留在殿中,封闭起来;考试时立即分发。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为的干扰。那些需要回答策略的人,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由高选的台省官员亲自监督。还要严禁他们相互勾结,考试结束后才离开。违反规定的,无论罪行大小,都不宽恕。这样,靠关系和请托的行为就被堵塞了。明君依靠自己不被欺骗,而不是依靠别人不欺骗自己。为什么要因为制定这样的制度而感到羞耻呢?如果确立了考试经学的法规,那么天下就可以不设立学官,人们自然会勤奋和快乐。
关于四科考试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现在在职的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不知道法律。有的法律条文难以理解,而小官吏又多是不知礼节的,让他们断案,无法把生死大事委托给他们,把百姓的生命交付给无知的人。作为官员不知道法律,被下属欺骗却不知道,又决定他们的命运,愤怒得不知道如何遵守法律,与不知道法律一样,不把事情交给负责人。或者凭自己的意思断案,因为不小心而违反法律,也可以让廉洁的官员像考试经学一样,对那些精通法律的人进行考试,优秀的人按照才能和品德进行任用。这样,天下就会减少违法的官员和错误的判决。
至于那些天生喜欢古代文化,心中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学习不是为了谋取俸禄,品味学问而忘记贫穷,就像高卿周生烈那样的人。学习精深而不追求名利的人,只有万分之一。至于像甯越、倪宽、黄霸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努力研究经典,并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因为困苦和劳累,想要通过经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汉武帝的时代,那么像朱买臣、严助那样的人,也不一定读书。现在如果想要通过读书来获得富贵,幸好有容易学习的方法,但如果本来就没有这种天生的喜好,怎么会愿意自己辛苦努力,拿着扫帚当学生,远行寻找老师学习呢?
在战争频繁的时代,武人受到重视,文人受到冷落,普通人把儒士看作仆人奴隶,把经书看作无足轻重的尘埃,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声名和这些不符。不学习就像是把帽子卖给夷人,把长须卖给华夏人。现在如果远近都一样,明确考试考核,那么一定会有人背负行囊千里迢迢去寻找老师和朋友,转而用送礼的钱财来购买书籍,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审举-注解
华霍:华霍,指华山和霍山,这里是比喻高大的山岳,象征着崇高的地位和成就。
崇极天之峻:崇极天之峻,指达到极高的地位,如同天空之高。
唐虞:唐虞,指古代的唐尧和虞舜,是传说中的圣贤君主。
臻巍巍之功:臻巍巍之功,指达到伟大的成就。
股肱之良:股肱之良,比喻得力的助手或忠诚的部下。
孙阳:孙阳,相传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善于相马的人,这里比喻有才能的人。
骐骥:骐骥,指骏马,比喻有才能的人。
千里:千里,指非常远的距离,这里比喻极大的成就。
稽古之才:稽古之才,指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人才。
宣力之佐:宣力之佐,指能够施展才能、辅助国家的人才。
凝庶绩:凝庶绩,指积累各种功绩。
人君:人君,指君主。
神鉴未兆:神鉴未兆,指具有超凡的洞察力,能够预见未来。
万机:万机,指国家大事。
康是赞:康是赞,指国家安定、得到赞扬。
槐棘:槐棘,指古代的官职,这里泛指各种官职。
皂隶:皂隶,指低级的官吏或仆役。
论道经国:论道经国,指讨论治国之道。
曲碎:曲碎,指琐碎的小事。
遐览:遐览,指远见。
广听:广听,指广泛听取意见。
有司:有司,指官员。
康:康,指国家安定。
赞:赞,指辅助。
孙阳之手:孙阳之手,指孙阳的相马之术。
骐骥之足:骐骥之足,指骏马的好脚力。
贡举之士:贡举之士,指通过贡举制度选拔的士人。
四科:四科,指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四个科目:经义、史书、子集、诗赋。
三事九列:三事九列,指古代官制中的三公九卿。
简标颖拔萃之俊:简标颖拔萃之俊,指选拔出优秀的才俊。
汉之末叶:汉之末叶,指汉朝末年。
桓灵之世:桓灵之世,指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时期。
柄去帝室:柄去帝室,指政权脱离皇帝的控制。
政在奸臣:政在奸臣,指政权掌握在奸臣手中。
网漏防溃:网漏防溃,指法网疏漏,防范不严。
风颓教沮:风颓教沮,指风气败坏,教育受阻。
清德:清德,指高尚的品德。
谄媚:谄媚,指奉承讨好。
履道:履道,指遵循正道。
多财:多财,指财富。
力竞成俗:力竞成俗,指争权夺利成为风气。
无耻:无耻,指不知羞耻。
宝:宝,指珍贵的东西,这里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东西。
书:书,指推荐信或关系。
望门而辟命:望门而辟命,指通过攀附权贵获得官职。
低头屈膝:低头屈膝,指卑躬屈膝,讨好他人。
积习而见收:积习而见收,指长期形成的习惯得到认可。
铨衡:铨衡,指衡量人才的标准。
斗斛:斗斛,古代的量器,这里比喻标准。
绳墨:绳墨,指墨线,这里比喻标准。
准格:准格,指准则和规格。
倾侧:倾侧,指倾斜,这里比喻不公正。
滓杂实繁:滓杂实繁,指杂质多,混乱。
虐暴:虐暴,指残暴。
豺贪:豺贪,指贪婪如豺狼。
聚敛:聚敛,指搜刮民财。
买官:买官,指通过金钱购买官职。
党援:党援,指结党营私,互相支持。
夜光:夜光,指夜间发光的宝石,这里比喻珍贵的人才。
澄浊飞沉:澄浊飞沉,指澄清是非,区分优劣。
沙汰:沙汰,指淘汰。
臧否:臧否,指评论人物的好坏。
严试对之法:严试对之法,指严格的考试制度。
峻贪夫之防:峻贪夫之防,指严厉防止贪污。
殄瘁攸阶:殄瘁攸阶,指消除疲惫和忧虑的途径。
诸侯贡士:诸侯贡士,指古代诸侯国向中央朝廷推荐的士人。
增班进爵:增班进爵,指提升官职和爵位。
黜位削地:黜位削地,指贬低官职和剥夺封地。
大车素餐:大车素餐,指不劳而获的人。
伐檀罝兔:伐檀罝兔,指捕猎兔子的人,这里比喻有才能的人。
负乘之患:负乘之患,指负担重,有风险。
翘秀:翘秀,指才能出众的人。
藏器以待贾:藏器以待贾,指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
琐碌:琐碌,指平庸无奇的人。
轻薄:轻薄,指轻浮浅薄的人。
人事以邀速:人事以邀速,指通过人际关系来追求快速成功。
鸟鸱:鸟鸱,指乌鸦,这里比喻邪恶之人。
鸳凤:鸳凤,指凤凰,这里比喻贤良之人。
麒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仁兽,这里比喻有德行的人。
不仁者远矣:不仁者远矣,指没有仁德的人会被远离。
奸伪荣显:奸伪荣显,指奸诈伪善的人得到荣耀和显赫。
英杰潜逝:英杰潜逝,指英雄豪杰隐退。
高概:高概,指高尚的节操。
阘茸:阘茸,指低贱之人。
饕餮:饕餮,古代传说中的贪食神,这里比喻贪婪之人。
括囊:括囊,指藏起才能,不表现出来。
凶邪相引:凶邪相引,指邪恶之人互相吸引。
小人道长:小人道长,指小人之道盛行。
梼杌:梼杌,古代传说中的凶恶之人,这里比喻坏人。
颂声:颂声,指赞美的声音。
怨嗟:怨嗟,指怨恨和叹息。
高干长材:高干长材,指才能出众的人。
逸伦之士:逸伦之士,指才能超群的人。
山峙渊渟:山峙渊渟,指山高水深,比喻才能深厚。
驰逐之徒:驰逐之徒,指追逐名利的人。
蔽而毁之:蔽而毁之,指被掩盖和诋毁。
奇才:奇才,指非常出众的人才。
稷卨之器:稷卨之器,指有才能的人。
邈世之量:邈世之量,指高远的气度。
沈滞:沈滞,指才能被埋没。
登叙:登叙,指得到提升和任用。
灵献之世:灵献之世,指东汉末年的灵帝时期。
阉官:阉官,指宦官。
台阁:台阁,指朝廷。
州郡:州郡,指地方行政区域。
牧守:牧守,指地方官员。
秀才:指科举考试中的生员,即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孝廉:指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两个科目,孝廉和秀才。
疾:疾,指疾病,这里指问题。
悬爵:悬爵,指空悬的爵位,这里指虚假的荣誉。
列肆:列肆,指市场。
市人:市人,指市场上的商人。
直者:直者,指正直的人。
空拳者:空拳者,指没有能力的人。
东园:东园,指东汉末年的宦官集团。
崔烈:崔烈,东汉末年的宦官。
铜臭:铜臭,指铜钱的臭味,这里比喻财富的腥臭。
上为下效:上为下效,指上级的行为对下级有示范作用。
君行臣甚:君行臣甚,指君主的行为对臣子有很大的影响。
阿佞幸:阿佞幸,指奉承君主的人。
亲容:亲容,指亲近君主。
桑梓:桑梓,指家乡。
中正:中正,指公正无私的人。
吏部:吏部,古代官署,负责官员的选拔和任用。
魁侩:魁侩,指中间人,这里指负责评定官员价值的人。
估:估,指评定价值。
清贫之士:清贫之士,指贫穷而清白的人。
陆沈:陆沈,指沉没,这里指被埋没。
履径:履径,指遵循正道。
知变:知变,指懂得变化。
方:方,指方法。
风姿丰伟:风姿丰伟,指外表英俊潇洒。
雅望:雅望,指良好的声誉。
干植:干植,指才能和基础。
貌取:貌取,指以貌取人。
仓卒:仓卒,指匆忙,这里指草率。
审良才於未用:审良才於未用,指在人才未使用之前就能识别他们的才能。
保性履之始终:保性履之始终,指保持自己的性格和品德到始终。
属托:指通过关系和权力来获得好处。
利欲:利欲,指贪图利益和欲望。
属托屈:属托屈,指屈服于关系。
澄思以察之:澄思以察之,指深思熟虑地去观察。
博访以详之:博访以详之,指广泛咨询并详细了解。
修其名而考其行:修其名而考其行,指考察一个人的名声和行为。
校同异以备虚饰:校同异以备虚饰,指比较相同和不同之处,防止虚假装饰。
孝友:孝友,指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
信义:信义,指诚信和道义。
小仕:小仕,指担任小官职。
忠清之效:忠清之效,指忠诚清廉的表现。
治事之干:治事之干,指处理事务的能力。
寸锦:寸锦,指一点点的才能。
刺鼠:刺鼠,指捉老鼠,这里比喻勇敢的行为。
策:策,指对策,这里指考试中的对策。
罪对:罪对,指错误的回答。
罚禁锢:罚禁锢,指惩罚并禁止担任官职。
刺史:刺史,古代地方行政区域的长官。
太守:太守,古代地方行政区域的长官。
左迁:左迁,指降职。
濮上:濮上,指古代地名,这里指音乐。
巴人:巴人,古代巴国的音乐,这里指音乐。
正音:正音,指正确的音乐。
腠理:腠理,指皮肤纹理,这里比喻细节。
退走:退走,指逃避问题。
干植不足:干植不足,指才能和基础不足。
徐徐:徐徐,指慢慢地。
公坐:指官场中的职务犯罪,即公职人员违反法律的行为。
贪浊:指贪污腐败,贪婪而不廉洁。
赃污:指贪污所得的财物。
夷齐:指古代的贤人伯夷和叔齐,此处比喻不廉洁的官员应该像他们一样隐居。
盗跖:指古代的盗贼,此处比喻贪污腐败的官员如果不受惩罚,就会变成盗贼。
贡士:指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人。
对策:指科举考试中回答皇帝或考官提出的问题。
对策无失指:指回答问题准确无误。
对策无脱谬:指回答问题没有错误。
经术:指儒家经典的研究和学问。
《洪范》:指《尚书》中的一篇,内容涉及治国之道。
箕子:指商朝末年的贤臣箕子,此处比喻有治国才能的人。
九术:指古代治国九术,即九种治国方法。
范生:指古代的贤人范雎,此处比喻有治国才能的人。
治国之略:指治理国家的策略。
夷吾: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此处比喻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
拨乱:指治理混乱。
不害:指不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霸王之道:指称霸天下的治国之道。
贡举:指古代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禁锢:指限制或禁止某人从事某种活动。
苛:指过分严厉。
繁策:指过于繁琐的管理方法。
伯乐:指古代著名的相马专家,此处比喻善于发现人才的人。
德政:指仁德的政治。
格言:指有教育意义的警句。
庸人:指平庸的人。
高文:指高深的文学。
顽夫:指固执的人。
箕子有经世之器:指箕子具有治理国家的才能。
范生怀治国之略:指范雎怀有治理国家的策略。
拨乱之干:指拨乱反正的能力。
精霸王之道:指精通称霸天下的治国之道。
长益风教:指长期有益于风俗教化。
私货:指非法所得的财物。
役:指使用或任用。
庶官:指各种官职。
旷:指空缺或未被填补。
贡举之法:指科举考试的规定。
苛而且重:指过于严厉且严重。
急贡举之法:指加强科举考试的规定。
禁锢之罪:指被禁锢的罪行。
急辔繁策:指过于急迫和繁琐的管理方法。
密防峻法:指严密防范和严厉的法律。
德政之所耻:指不符合德政的行为。
骨填肉补:指用骨头和肉来填补身体。
养体益寿:指保养身体,延年益寿。
日曷溺之急:指非常紧急的情况。
宽含垢之政:指宽容包容的政治。
莅敦御朴:指亲自管理并保持朴素的治理方式。
拯衰弊之变:指拯救衰败和弊端。
挥戈奋剑:指拿起武器战斗。
弹琴咏诗:指弹奏乐器和吟唱诗歌,此处比喻无能为力。
燎火及室:指火势蔓延到房屋。
奔走灌注:指迅速行动并采取措施。
揖让盘旋:指谦让和徘徊不前。
跖议捕盗:指盗贼讨论如何捕捉其他盗贼,此处比喻不切实际。
九垓:指极远的地方,此处比喻整个国家。
王制政令:指国家的法律和政令。
齐一:指统一。
江表:指长江以南的地区。
道化:指道德教化。
率礼教:指遵循礼仪教化。
千余载:指一千多年。
子游仲任:指古代的贤人子游和仲任,此处比喻有德行才学的人。
上国:指中原地区,此处指中央政府。
吴土:指古代的吴国地区。
贡士见偃以不试:指吴国的贡士因为不参加考试而被废黜。
太平:指社会安定和平的时代。
东南儒业:指东南地区的儒家学术。
左衽:指古代的一种服装,此处指不同地区的人。
儒学之事:指儒家学术的研究和传承。
中州:指中原地区。
甯越倪宽黄霸之徒:指古代的学者甯越、倪宽和黄霸,此处比喻通过勤奋学习而成功的人。
典籍:指经典书籍。
患苦困瘁:指困难和劳累。
经术自拔:指通过学习经典来提升自己。
朱买臣严助之属:指古代的学者朱买臣和严助,此处比喻通过学习而成功的人。
汉武之世:指西汉武帝时期。
易於学者:指容易学习。
素无自然之好:指没有天生的兴趣。
空自勤苦:指徒劳无功。
执洒埽:指做仆役的工作。
寻师问道:指寻找老师学习知识。
负笈千里:指背着书箱走千里路。
礼赂:指礼物和贿赂。
记籍:指书籍。
负笈:指背着书箱。
台阁主者:指中央政府的官员。
诬枉:指冤枉。
执事:指负责某项事务的人。
防:指预防。
豫作:指提前准备。
禁其留草殿中:指禁止将草稿留在宫殿中。
亟赋之:指立即命题。
绝:指断绝。
翼窒:指堵塞。
不可欺:指不可被欺骗。
峻为斯制:指严格制定这些制度。
了不试:指完全不尝试。
了:同“了”,完全。
案四科:指按照四个科目来考核。
明解法令:指明确理解法律。
决狱:指审理案件。
轻百姓之命:指轻视百姓的生命。
付主者:指交给主管的人。
蹉跌:指错误。
廉良之吏:指廉洁善良的官员。
明律令:指明确法律和命令。
叙用:指任用。
弄法之吏:指违法的官员。
失理之狱:指不公正的审判。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外篇-审举-评注
此段古文出自《抱朴子》,作者葛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和医学家。这段文字主要论述了贡举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选拔人才,维护社会秩序。
‘又,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这句话强调了对于官员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特别是对于贪污腐败的行为,即使不致死,也要终身禁锢,以示警戒。
‘如此,不廉之吏,必将化为夷齐矣。’这句话通过比喻,说明严厉的法律可以使得不廉洁的官员转变为廉洁之士,体现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若临官受取,金钱山积,发觉则自恤得了,免退则旬日复用者,曾史亦将变为盗跖矣。’这句话进一步强调了法律对于官员廉洁自律的重要性,即使曾经廉洁的官员,如果贪污腐败,也会变成盗跖。
‘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质疑,即仅仅通过考试就能选拔出真正有政治才能的人才吗?
‘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抱朴子以古代通过射箭来选拔人才为例,说明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可行的。
‘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这句话通过比喻,说明了人才需要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才能成长。
‘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暗蔽也。’这句话强调了考试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性,通过考试可以避免人才的暗蔽。
‘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之以对策,况文士乎?’这句话通过对比,说明了即使是良将也需要通过复试来选拔,那么对于文士来说,考试更是必要的。
‘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这句话强调了贡举制度对于促进学习的积极作用。
‘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这句话提出了贡举制度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作用,通过选拔人才,可以减少私货,使奇才得以发挥,官员不致空缺。
‘或曰:“先生欲急贡举之法,但禁锢之罪,苛而且重,惧者甚众。”’这句话提出了对于贡举制度过于严厉的担忧。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补之药,长於养体益寿,而不可以救日曷溺之急也。”’抱朴子以药物为例,说明了贡举制度虽然严格,但也是为了培养人才,不能因为过于严厉而忽视其积极作用。
‘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这句话强调了统一的政治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这句话说明了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於在昔也。’这句话指出了吴地贡举制度不健全,导致东南地区儒学衰落。
‘所谓饶之适足以败之者也。’这句话强调了过于宽松的政策反而会导致问题的恶化。
‘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这句话强调了真正的学者应该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今若遐迩一例,明考课试,则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这句话说明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可以促进学术的繁荣。
‘抱朴子曰:才学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这句话表达了对于人才稀缺的担忧。
‘常追恨於时执事,不重为之防。’这句话表达了对于当时官员不重视贡举制度的遗憾。
‘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这句话提出了对于贡举制度的改革建议。
‘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於峻为斯制乎?’这句话强调了明君应该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依赖他人的诚信。
‘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矣。’这句话提出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减少学官的必要性。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这句话指出了当时官员对于法律的忽视。
‘或以意断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这句话提出了对于官员进行法律考试的改革建议。
‘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这句话表达了通过法律考试可以减少官员违法行为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