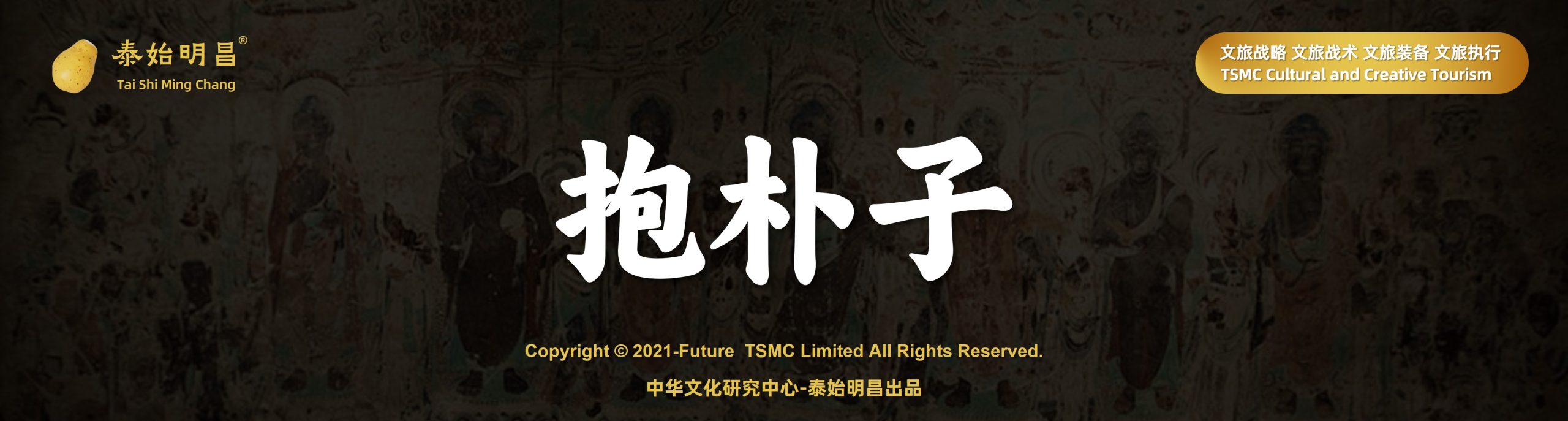作者: 葛洪(283年-363年),字君复,号抱朴子,晋代的道家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道家学术理论,还在于医学和炼丹术的研究。葛洪提出了许多关于长生不老、修身养性的理论,他的作品在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年代:成书于晋代(约365年)。
内容简要:《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集中讲述了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了长生不老的秘方和如何通过修炼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外篇》则多涉及炼丹术、医学、治病等实际操作。葛洪在书中不仅总结了自己关于炼丹和修道的经验,还提出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通过修身养性与练气,个人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甚至实现延年益寿。书中的医药学内容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医学与道家文化的珍贵遗产。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内篇-勤求-原文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
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
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须人求之至勤者,犹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笃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
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或呼为鬼魅之变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岂有肯谓修为之所得哉?
苟心所不信,虽令赤松王乔言提其耳,亦当同以为妖讹。
然时颇有识信者,复患於不能勤求明师。
夫晓至要得真道者,诚自甚稀,非仓卒可值也。
然知之者,但当少耳,亦未尝绝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广不笃,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世閒自有奸伪图钱之子,而窃道士之号者,不可胜数也。
然此等复不谓挺无所知也,皆复粗开头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饰伪,而好事之徒,不识其真伪者,徒多之进问,自取诳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广寻奇士异人,而告之曰,道尽於此矣。
以误於有志者之不少,可叹可恚也。
或闻有晓消五云、飞八石、转九丹、冶黄白、水琼瑶、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炉、采灵芝於嵩岳者,则多而毁之曰,此法独有赤松王乔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虚妄耳。
则浅见之家,不觉此言有诈伪而作,便息远求之意。
悲夫,可为慨叹者也!
凌晷飙飞,暂少忽老,迅速之甚,谕之无物,百年之寿,三万馀日耳。
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耄,除数十年,而险隘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咄嗟灭尽,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於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
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
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
里语有之:人在世閒,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
此譬虽丑,而实理也。
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於事。
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
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
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
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
今察诸有此谈者,被疾病则遽针灸,冒危险则甚畏死。
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诰而治子书,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则谓之朴野,非老庄之学。
故无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说,而不能自返也。
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於摇尾涂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
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
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壤合体,令人怛然心热,不觉咄嗟。
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业哉?
其不信则已矣。
其信之者,复患於俗情之不荡尽,而不能专以养生为意,而营世务之餘暇而为之,所以或有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
凡人之所汲汲者,势利嗜欲也。
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
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
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
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数百岁,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
然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
昔汉太后从夏侯胜受尚书,赐胜黄金百斤,他物不可胜数。
及胜死,又赐胜家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一百日。
成帝在东宫时,从张禹受论语。
及即尊位,赐禹爵关内侯,食邑千户,拜光禄大夫,赐黄金百斤。
又迁丞相,进爵安昌侯。
年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钱数万。
及禹疾,天子自临省之,亲拜禹床下。
章帝在东宫时,从桓荣以受孝经。
及帝即位,以荣为太常上卿。
天子幸荣第,令荣东面坐,设几杖。
会百官及荣门生生徒数百人,帝亲自持业讲说。
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及荣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车,抱卷而趋,如弟子之礼。
及荣薨,天子为荣素服。
凡此诸君,非能攻城野战,折冲拓境,悬旌效节,祈连方,转元功,骋锐绝域也。
徒以一经之业,宣传章句,而见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说死人之餘言耳。
帝王之贵,犹自卑降以敬事之。
世閒或有欲试修长生之道者,而不肯谦下於堪师者,直尔蹴迮,从求至要,宁可得乎?
夫学者之恭逊驱走,何益於师之分寸乎?
然不尔,则是彼心不尽;
彼心不尽,则令人告之不力;
告之不力,则秘诀何可悉得邪?
不得已当以浮浅示之,岂足以成不死之功哉?
亦有人皮肤好喜,而信道之诚,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阳为曲恭,累日之閒,怠慢已出。
若值明智之师,且欲详观来者变态,试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测其志。
则若此之人,情伪行露,亦终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尽言吐实,言不了则为之无益也。
陈安世者,年十三岁,盖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
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贵,先得道者则为师矣,吾不敢倦执弟子之礼也。
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复仙去矣。
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禀气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师,告之以度世之道,则无由免死,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颓矣。
由此论之,明师之恩,诚为过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
可不求之乎?
抱朴子曰:
古人质正,贵行贱言,故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辞说。
风俗衰薄,外饰弥繁,方策既山积於儒门,而内书亦鞅掌於术家。
初学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
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为快。
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诫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
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
杂猥弟子,皆各随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远,察其聪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岁中,时有尽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
或但将之合药,药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终年不以其方文传之。
故世閒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
而管见之属,谓仙法当具在於纷若之书,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
夫长生制在大药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汉二代,大兴祈祷,所祭太乙五神,陈宝八神之属,动用牛羊穀帛,钱费亿万,了无所益。
况於匹夫,德之不备,体之不养,而欲以三牲酒餚,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
或颇有好事者,诚欲为道,而不能勤求明师,合作异药,而但昼夜诵讲不要之书,数千百卷,诣老无益,便谓天下果无仙法。
或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死丧相袭,破产竭财,一无奇异,终不悔悟,自谓未笃。
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师,以此之费,给买药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长生度世也。
何异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仓之收,用力虽尽,不得其所也。
所谓適楚而道燕,马虽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
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聪明不足以校练真伪,揣测深浅;所博涉素狭,不能赏物。
後世顽浅,趣得一人,自誉之子,云我有秘书,便守事之。
而庸人小儿,多有外讬有道之名,名过其实,由於夸诳,内抱贪浊,惟利是图,有所请为,辄强喑呜,俛仰抑扬。
若所知宝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状。
其有所请,从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许以顷後,故使不觉者,欲罢而不能,自谓事之未勤,而礼币之尚轻也。
於是笃信之心,尤加恭肃,赂以殊玩,为之执奴仆之役,不辞负重涉远,不避经险履危,欲以积劳自效,服苦求哀,庶有异闻。
而虚引岁月,空委二亲之供养,捐妻子而不恤,戴霜蹈冰,连年随之,而妨资弃力,卒无所成。
彼初诚欺之,末或惭之,懵然体中,实自空罄短乏,无能法以相教,将何法以成人乎?
余目见此辈不少,可以有十餘人。
或自号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谓之已三四百岁,但易名字,诈称圣人,讬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书其人之姓名耳。
颇游俗閒,凡夫不识妍蚩,为共吹扬,增长妖妄,为彼巧伪之人,虚生华誉,歙习遂广,莫能甄别。
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两耳者,误於学者,常由此辈,莫不使人叹息也。
每见此曹,欺诳天下,以规势利者,迟速皆受殃罚,天网虽疏,终不漏也。
但误有志者可念耳。
世人多逐空声,鲜能校实。
闻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许,必当有异,便载驰竞逐,赴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
而不复寻精,彼得门人之力。
或以致富,辨逐之虽久,犹无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与悟,自可悲哉!
夫搜寻仞之垄,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鳞,用日虽久,安能得乎?
嗟乎!将来之学者,虽当以求师为务,亦不可以不详择为急也。
陋狭之夫,行浅德薄,功微缘少,不足成人之道,亦无功课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劳也。
抱朴子曰:“诸虚名之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於不知,阳若以博涉已足,终不肯行求请问於胜己者,蠢尔守穷,面墙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复憎忌於实有道者而谤毁之,恐彼声名之过己也。此等岂有意於长生之法哉?为欲以合致弟子,图其财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听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贫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贱者不可虚云我贵也,况道德之事实无,而空养门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犹不宜怀妒善之心,况於道士,尤应以忠信快意为生者也,云何当以此之亻敝然函胸臆閒乎?人自不能闻见神明,而神明之闻见己之甚易也。此何异乎在纱幌之外,不能察轩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谓人之不见己。此亦如窃锺枨物,铿然有声,恶他人闻之,因自掩其耳者之类也。而聋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专擅华名,独聚徒众,外求声价,内规财力,患疾胜己,乃剧於俗人之争权势也。遂以唇吻为刃锋,以毁誉为朋党,口亲心疏,貌合行离,阳敦同志之言,阴挟蜂虿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恶,招祸之符檄也。
夫读五经,犹宜不耻下问,以进德修业,日有缉熙。至於射御之粗伎,书数之浅功,农桑之露事,规矩之小术,尚须师授以尽其理,况营长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与救恤死事无异也。何可务惜请受之名,而永守无知之困,至老不改,临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笃暗者也。
令人代之惭悚,为之者独不顾形影也。为儒生尚当兀然守朴,外讬质素,知而如否,有而如无,令庸儿不得尽其称,称而不问不对,对必辞让而後言。
何其道士之人,强以不知为知,以无有为有,虚自衒燿,以图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耻改也。
吾非苟为此言,诚有为而兴,所谓疾之而不能默然也。
徒愍念愚人,不忍见婴儿之投井耳。
若览之而悟者,亦仙药之一草也,吾何为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诊而可知者也。
抱朴子曰:“设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
今杂猥道士之辈,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长生可知也。
虽治病有起死之效,绝穀则积年不饥,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视千里,知人盛衰,发沈祟於幽翳,知祸福於未萌,犹无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请求,耻事先达,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极之痛,是不见事类者也。
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
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
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
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
夫治国而国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
惜短乏之虚名,耻师授之蹔劳,虽日不愚,吾不信也。
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犹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轻,脱炙烂而保视息,甘其苦痛,过於更生矣。
人但莫知当死之日,故不暂忧耳。
若诚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将为之。
况但躬亲洒扫,执巾竭力於胜己者,可以见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为苦,而蔽者惮焉。
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烧爇,羞逃风而致沈溺於重渊者,世必呼之为不晓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灾危,而莫怪其不畏实祸,何哉?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
实欲令迷者知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坠井引绠,愈於遂没。
但惜美疢而距恶石者,不可如何耳。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日月之蚀,睎颜氏之子也。
又欲使将来之好生道者,审於所讬,故竭其忠告之良谋,而不饰淫丽之言。
言发则指切,笔下则辞痛,惜在於长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抱朴子曰:“深念学道艺养生者,随师不得其人,竟无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见彼之不得长生,因云天下之果无仙法也。
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约己以修玄妙者,亦徒进失干禄之业,退无难老之功,内误其身,外沮将来也。
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
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内篇-勤求-译文
抱朴子说:‘天地间最大的德行是生育万物,生育意味着喜欢万物。因此,道家最保密、最重视的,莫过于长生不老的方术。所以,用血盟誓来传承,如果传给不合适的人,会受到天罚的警告。先师不敢轻易传授给他人,只有那些非常勤奋求道的人,才会挑选最精纯的人来教导,何况那些不喜欢、不求道,或者求道不坚定的人,怎么可以炫耀自己的无知来欺骗别人呢?那些没有得到仙人真传的人,即使每天看到成群的仙人生活在世间,也一定会认为他们是从另一个种族来的人,或者认为这是天上的奇事,或者是偶然的自然现象,怎么会认为是修炼得到的呢?如果心中不信,即使赤松子、王乔这样的仙人亲自拉住他的耳朵,他也会认为那是妖言怪论。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有见识、有信仰的人,又苦于找不到明师。真正懂得至高真理、得到真道的人非常稀少,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但是,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也并没有在世间灭绝。这是因为求道的人不够广泛、不够坚定,有仙命的人,自然会有机会遇到明师。然而,求而不得的人是有的,但是没有不求就能得到的人。
世间自有那些奸诈、图谋钱财的人,他们冒充道士的名号,数量多得数不清。然而这些人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们有的只是初露头角,有的虚张声势,加上他们隐藏邪恶、伪装成真,那些喜欢热闹的人不辨真伪,纷纷前来请教,自讨苦吃,被他们误导,不能真正修行。他们四处寻找奇人异士,告诉他们:‘道就在这里。’这样误导有志向的人,真是令人叹息。
有些人听说有懂得消散五云、飞八石、转九丹、炼黄白、水琼瑶、化朱碧、在神炉中凝结霜雪、在嵩山采集灵芝的人,就纷纷毁谤说:‘这些方法只有赤松子、王乔知道,现在世上有的人说知道,都是胡说八道。’那些见识浅薄的人,不辨真假,就放弃了远求真道的念头。真是可悲啊,这真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情!
时光飞逝,人从年轻到衰老,变化之快,就像是没有东西一样,百年的寿命,不过三万多个日子。年幼时不懂事,年老时快乐和欢乐都消失了,童年和老年,除去这数十年,剩下的时间,又有多少是被危险、忧虑和疾病占据的,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半。能够活到百岁的,喜笑平和的,也不过五六十年,转眼间就过去了,哀伤和昏庸,又有六七千天,转眼间也就过去了,即使能够活到百岁的人,也是万中无一。
仔细想想,也不必嘲笑那些夏天的虫子和早晨的蘑菇。因为不知道的人,实在是太可悲了。有句俗语说:‘人在世间,一天天失去一天,就像牵着牛羊去屠宰场,每前进一步,离死亡就更近一步。’这个比喻虽然有些丑陋,但却是真理。通达的人之所以不担忧死亡,不是因为不想求道,而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避免死亡,空自烦恼,对事情没有帮助。所以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并不是不想长生。
周公请求代替武王,孔子拄着拐杖悲伤,这说明即使是圣人,也不愿意早早地死去。俗人看到庄子有关于大梦的比喻,于是纷纷争论生死的问题。这大概是歪门邪道,故意说出违背常理的话,这正是孔子所批评的。
现在看看那些有这种说法的人,他们一旦生病就急忙针灸,遇到危险就非常害怕死亡。然而,末世的风气普遍不崇尚真实和信仰,背离经典和教诲,治理学问,如果不吐露反常的巧妙辩论,就被认为是质朴无华,不是老庄的学问。所以,没有骨气而追求世俗之徒,就流连于错误的说法,而不能自拔。
老子把长生久视为自己的事业,而庄子却看重在泥水中摇尾巴的生活,不愿意成为被网捕获的乌龟,被绣花装饰的牛,饿着肚子向河伯求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能真正看淡生死。
晚辈学者不能辨别真伪,只根据一句话就断定,这不是很荒谬吗?
深入九泉之下,漫长的黑夜无边无际,一开始成为蝼蚁的食物,最终与尘土融为一体,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不禁叹息。如果有求生的愿望,为什么不放下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去修炼玄妙之道呢?如果不信,那就罢了。如果相信,又苦于世俗的情感不能完全放下,不能专心致志地养生,只能在处理世事之余,稍作修炼,所以,即使有人去修炼,也常常因为年老而多不成功。
人们所追求的,大多是权势和欲望。如果身体不完整,即使有高官厚禄,金玉满山,美女如云,也不是自己的。因此,上士首先追求长生不老的事情,长生不老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如果还没有升入玄妙之境,去世之前,可以先在仙人之间游历。像彭祖、老子这样的人,在人世间活了几百年,也没有失去人的乐趣,然后慢慢地去世,这也是一件大事。但是,一定要有好的师傅,如果师傅不够好,也就无法成就长生不老的事业。
过去,汉太后从夏侯胜那里学习尚书,赐给夏侯胜黄金百斤,其他东西数不胜数。等到夏侯胜去世后,又赐给夏侯胜家钱二百万,为夏侯胜服丧一百天。成帝在东宫时,从张禹那里学习论语。等到成帝即位,赐给张禹关内侯的爵位,食邑千户,任命他为光禄大夫,赐黄金百斤。后来又升任丞相,进封为安昌侯。年老后请求辞官,赐给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钱数万。等到张禹生病,天子亲自去探望,亲自拜见张禹的床下。章帝在东宫时,从桓荣那里学习孝经。等到章帝即位,任命桓荣为太常上卿。天子到桓荣的家中,让桓荣面向东坐,摆放几案和手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皇帝亲自拿着经书讲解。赐给桓荣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五千户。等到桓荣生病,天子亲自到他的家中,进入小巷下车,拿着卷子快步走去,就像弟子一样。等到桓荣去世,天子为桓荣服丧。
这些人都不是能攻城掠地、开拓疆域、悬挂旗帜、效忠国家、转战四方、建立功勋、在遥远的地方显示锐气的人。他们只是凭借一门学问,传播经文,却受到尊重,威严如此,这只是为了说死人的话而已。帝王的尊贵,也还要自卑地降低身份去尊敬他们。世间有些人想要尝试修炼长生之道,却不愿意向可敬的师傅谦卑,只是盲目地追求最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得到呢?学者谦逊的态度,对师傅的尊重,有什么用呢?如果不这样,那就说明他们的心还不够虔诚;如果心不虔诚,那么教诲他们的人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教诲不力,那么秘诀又怎么能完全掌握呢?不得已的时候,只能用浅显的东西来教他们,这怎么能成就长生不老的事业呢?
也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喜欢,但信仰不真诚,不深入心灵,有所求而表现出虚伪的恭敬,连续几天,就会变得懒散。如果遇到明智的师傅,就会详细观察来者的变化,用时间来考验,所以不立即告诉他们,来测试他们的志向。如果这样的人,虚伪的行为暴露无遗,最终也不会得到教导,即使得到了教导,也不会完全说出真相,说了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安世,十三岁时,是盖灌叔本家的客人,先得到了仙道。叔本七十岁时头发花白,早晚都拜见安世说:‘道尊德贵,先得到道的人就是师傅了,我不敢懈怠地遵守弟子之礼。’因此,安世把重要的方术传授给他,然后又成仙去了。
人生先从天地那里得到精神,后从父母那里得到气血,如果没有明师,告诉他们度世的方法,就没办法避免死亡,就像凿石头有余温,寿命已经衰老了。
由此看来,明师的恩情,确实超过天地,比父母还要重要,怎么能不尊重他们,不寻求他们呢?
抱朴子说:‘古人性格质朴正直,重视行为而轻视言语,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崇尚文辞辩论,修道的人不推崇辞藻华丽的说法。风俗逐渐衰败,外在装饰越来越多,策略和方术在儒家和道家之间积累如山,初学者还没有资格传授这些重要的东西。人们都喜欢那些知识丰富的人。所以后来研究道的人,如干吉、容嵩、桂帛等各家,各自著书立说,但大多只是教诲之言,不愿意很好地向人开示大道的宗旨。那些真正重要的秘诀,有的只是口头传授,有的不过是一尺长的布条,藏在衣带中,不是跟随师傅长时间、勤奋地尝试,是得不到的。杂乱无章的弟子,各自根据自己的用心程度、忍受痛苦的久远程度,观察他们的聪明才智所能达到的,以及他们的志向和能力,分别传授。千百年来,有些人甚至把所有的秘籍都藏在自己的枕头和袖子下面,这些秘籍的精髓。有的人只是用这些秘籍来配制药物,药物成分足以使人不死,但整年都不把这些方子写下来。所以世间的道士,知道金丹之事的,万中无一。而那些自诩知道仙法的人,认为仙法就在那些纷繁的书籍和祭祀跪拜之间。长生的关键在于大药,不是通过祭祀就能得到的。过去秦汉两代,大兴祈祷,祭祀太乙五神、陈宝八神等,动用牛羊谷物丝绸,花费亿万,却没有任何益处。何况普通人,德行不备,身体不养,却想用三牲酒食,祈求鬼神,以求延年益寿,这种迷惑也太大了。有的人虽然喜欢修道,但不能勤奋地寻找明师,合作炼制异药,只是昼夜不停地诵读那些无用的书籍,成千上百卷,到老也没有益处,于是说天下果然没有仙法。有的人甚至跪地磕头,向空无一人的座位祈求,宰杀牲畜,烧香祈福,但病人不愈,死丧相继,破产耗尽家财,一无所得,最终也不悔悟,自认为还不够虔诚。如果用这样的勤奋去寻找懂得方术的师傅,用这样的花费去购买药物,也一定能得到神仙长生之道。这和到老还在空旷的石田里耕作,却希望收获千仓的粮食一样,虽然用力尽力,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这就是所说的‘到楚国却走燕国的路’,马虽然好,但因为路线错了,所以到不了目的地。有的人性格忠诚,喜欢相信别人,但他们的聪明才智不足以辨别真伪,无法判断深浅;他们涉猎的范围很窄,不能欣赏事物。后世的人愚昧浅薄,一旦找到一个人,自称为有秘籍,就盲目地追随。而那些平庸无知的人,多有假托有道的名声,名声超过实际,因为夸大其词,内心贪婪污浊,只追求利益,一旦有人请求,就装模作样,或点头或摇头,好像自己掌握了深不可测的秘籍。对于请求,他们总是满足对方的要求,点头微笑,或许答应在以后某个时候给予,这样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想要放弃却不能,自认为还不够努力,礼金还不够重。于是,他们更加虔诚恭敬,用珍奇的玩物作为贿赂,为他们做奴仆的活儿,不辞劳苦,不怕艰险,想要通过积累劳苦来表现自己,忍受痛苦,希望得到一些不同的信息。他们虚度岁月,空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而不顾,冒着严寒和酷暑,年复一年地跟随,浪费了钱财和精力,最终一无所成。他们开始时确实是欺骗,后来也许会感到羞愧,但内心空虚,实际上什么也教不了,用什么方法来培养人呢?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人不少,可能有十几个。他们自称为高人,久居世间,世人或许认为他们已经活了几百岁,只是改了名字,假装成圣人,混迹于人群中,而很多人都会去追随他们,我只是不喜欢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经常在世俗之间游荡,普通人不识善恶,共同吹捧他们,助长了他们的妖妄,那些巧舌如簧的人,虚假地赢得了名誉,名声传播开来,没有人能够辨别。所以有时候,那些高人如果不留意澄清真相,只是任由自己的耳朵去接受,就会误信这些学者,常常因此叹息。每次看到这些人,欺骗天下,为了谋取利益,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受到天罚,天网虽然疏漏,但最终不会放过任何人。只是误导了有志向的人,令人感慨。世人大多追逐虚名,很少能够辨别真相。听说某人有很多弟子,多达几百人,一定有特别之处,于是纷纷追逐,去成为他的追随者,浪费了修炼的功夫,去重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再寻求精华,而那些人得到了门人的力量。有的人因此致富,尽管追查了很久,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道,愚昧的人因此不知道这些人不足以追随,怎么可能都不觉悟,真是可悲啊!寻找千仞高山上的树木,在牛迹中寻找吞舟之鱼,虽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怎么可能找到呢?唉!未来的学者,虽然应当以寻找师傅为要务,但也绝对不能不谨慎选择为首要任务。那些见识短浅、行为浅薄、功力微薄、缘分少的人,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也没有能力去满足他人的重恩。深思熟虑他们的兴趣,不要让他们徒劳无功。’
抱朴子说:‘那些只有虚名而没有真才实学的道士,既擅长说谎欺骗,来欺骗学习者;又常常掩饰自己的短处和愚昧,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感到羞耻,表面上好像自己涉猎广泛已经足够,却始终不愿意去向比自己强的人请教,愚蠢地守着贫穷,面对墙壁站立;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嫉妒那些真正有道德的人,并诽谤他们,害怕他们的名声超过自己。这些人哪里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呢?他们只是为了吸引弟子,图谋他们的财富,以满足自己的情欲罢了。然而他们不知道天高听卑,最终一定会受到这样的灾祸。贫穷的人不能胡说自己是富有的,地位低微的人不能虚称自己高贵,何况道德的实际并不存在,却空养门生弟子呢?普通人尚且不应该怀有嫉妒别人的心,更不用说道士了,他们更应该以忠诚、诚信和快乐为生,怎么会把这种丑陋的东西藏在心中呢?人自己不能听到神明的声音,但神明听到自己的声音却很容易。这就像在窗帘外面,不能看到房间里面的情况,却还傲慢地认为别人看不到自己一样。这就像偷钟敲鼓,声音很大,却害怕别人听到,于是自己捂住耳朵。那些精神上的聋子和瞎子,只想独占美名,聚集徒弟,外面追求名声,里面追求财富,害怕别人超过自己,这比普通人争权夺利还要严重。于是他们用言语为刀剑,用毁誉为朋党,口头上亲近,心里却疏远,表面上假装同心同德,实际上却怀着毒蛇般的恶意,这是天和人都厌恶的,是招来灾祸的征兆。读五经,还应该不耻下问,以提升道德修养,每天都有进步。至于射箭、驾车这样的粗浅技艺,书法、算术这样的浅显功夫,农事、桑事这样的露天工作,规矩、法则这样的小技巧,还需要师傅传授才能完全理解,何况是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想要延长寿命,这和救死扶伤没有区别。怎么可以为了保全名声而吝啬请教,永远陷入无知的困境,到老都不改变,临死都不后悔,这也是天民中的愚昧者。让人感到羞愧和害怕,而那些去做的人却毫不顾忌自己的形象和影子。
抱朴子说:‘如果有人犯了死罪,而有人能够救他,那个人一定不会因为劳累、羞辱和低声下气而吝啬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得到救人的功绩。现在那些杂乱无章的道士,得不到金丹的大法,就一定不能长生不老,这是可以预知的。虽然他们治病有起死回生的效果,断食可以多年不饿,役使鬼神,坐着就能消失,坐着就能出现,能看千里之外,能知道人的兴衰,能在暗处发现病根,能在未发生之前知道祸福,但这些对延长寿命还是没有帮助,他们还羞于行请求,耻于向有成就的人请教,这是珍惜一天的屈辱,却愿意忍受无尽的痛苦,这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的人。古人有句话说,生命对我很重要。从贵贱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帝王,也不足以用这种方法来相比。从轻重角度来看,即使是拥有天下的人,也不足以用这种方法来交换。所以有宁愿死为王而不愿做生鼠的比喻。治理国家而国家安宁,修养身体而身体健康,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都是通过某种方法才能达到的。珍惜那些虚名,耻于向师傅请教一点劳动,虽然表面上不显得愚蠢,但我是不相信的。现在如果有人能免除必死的命运而接受刑罚,还会高兴地离开重的刑罚而接受轻的刑罚,从火中解脱出来而保住生命,比重新出生还要高兴。人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死的那一天,所以不会暂时忧虑。如果真的知道那一天,即使是断肢、割鼻的事情,能够延迟,也一定会去做。何况只是亲自打扫,拿着毛巾尽力去帮助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可以学到不死的道理,这又有什么苦的呢?而那些愚蠢的人却害怕。
抱朴子说:‘过去写的道书很多,没有一个不是追求那些浮夸巧妙的言语,来推崇玄虚的宗旨,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勤奋地讨论长生不老的方法,批判修道中的弊端。实际上是想让那些迷失的人知道回头,失去的东西在东边,却在西边找回,掉进井里,拉起绳子,比继续沉没要好。只是可惜那些只看到美好的疾病,却拒绝恶石的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谁没有过错,过而能改,就像日蚀一样,是颜回那样的孩子。我还想让将来喜欢修道的人,能够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师傅,所以竭尽忠诚地给出好的建议,而不修饰华丽的言语,言语发出就直截了当,笔下就言辞犀利,珍惜的是长生不老,压制的是邪恶,还需要追求什么呢?’
抱朴子说:‘深深思考那些学习道术和养生的人,如果跟错了师傅,最终一无所成,让后来的有志者看到他们不能长生不老,于是说天下根本就没有仙法。凡是自己衡量自己,一定不能苦身节食来修炼玄妙之术的人,也只会白白浪费了求取功名利禄的机会,退一步说,也没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对内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对外阻碍了后来者的道路。成为仙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就像播种黍稷一样明显。然而没有不耕种就能得到好谷物的,没有不勤劳就能得到长生不老的。’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内篇-勤求-注解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性是产生万物,这里的‘生’指的是生命的产生和维持。
道家:指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强调顺应自然,追求长生不老。
长生之方:指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或方法。
血盟:古代一种通过割破手指,将血滴在盟书上,以示誓言的仪式。
先师:对前辈师长的尊称。
仙人: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人。
赤松王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伏邪饰伪:隐藏邪恶,伪装成善良。
五云:指五种颜色的云彩,常用来比喻美好的事物。
八石:指八种珍贵的石头,这里指珍贵的矿石。
九丹:指九种丹药,古代炼丹术中的术语。
黄白:指黄金和白银,古代炼丹术中的术语。
水琼瑶:指美玉,这里指珍贵的宝石。
朱碧:指红色和绿色,这里指颜色鲜艳的宝石。
霜雪:指寒冷的气候,这里指冰冷的石头。
神炉:指炼丹用的炉子。
灵芝:古代传说中的仙草,能延年益寿。
嵩岳:指嵩山,古代认为是有仙气的山。
夏虫朝菌:比喻见识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事物。
乐天知命:指顺应天命,乐观地接受一切。
姬公:指周公,周朝的贤臣。
武王: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君主。
仲尼:指孔子,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诡道强达:指用诡异的手段达到目的。
阳作违抑之言:指表面上做出违背常理的言论。
老庄:指老子和庄子,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九泉之下:指地底,这里指死后。
蝼蚁之粮:指被蝼蚁吃掉的食物,比喻生命短暂。
河侯:古代神话中的河伯,这里指河神。
玄妙之业:指修炼长生不老等神秘之事。
地仙人閒:指在人间修炼成仙。
彭祖:古代传说中的长寿仙人。
老子:指老聃,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昇玄去世:指修炼成仙,升天成仙。
堪师:合格的师傅。
浮浅:肤浅,不深入。
度世之道:指超脱生死的方法。
凿石有馀焰:比喻事情已经接近成功,但最终未能成功。
悬旌效节:指悬挂旗帜,表示效忠。
祈连方:指边远的地方。
转元功:指转换元气的功夫。
骋锐绝域:指在遥远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才华。
章句:指经书的段落。
关内侯:古代的一种爵位。
食邑:指封地,可以收取租税的地方。
光禄大夫:古代的一种官职。
祈连:古代的一个地名,指边远的地方。
元功:指伟大的功绩。
绝域:遥远的地方。
弟子之礼:学生对老师的尊敬礼节。
素服:白色的衣服,表示哀悼。
攻城野战:指战争中的攻城和野战。
折冲拓境:指在战争中击败敌人,开拓疆土。
一经之业:指精通一部经典。
里语:民间流传的谚语。
骨殖:指尸骨。
偶俗之徒:指追求世俗的人。
不然之说:指不符合常理的说法。
摇尾涂中:指比喻在世俗中迎合他人。
被网之龟:指被网捕的乌龟,比喻陷入困境。
被绣之牛:指被绣花装饰的牛,比喻外表华丽而实质空虚。
俗情:世俗的情感和观念。
世务:世俗的事务。
势利:追求权势和利益。
嗜欲:强烈的欲望。
上士:指品德高尚的人。
灌叔本:古代的一位仙人。
安世:古代的一位仙人。
精神:指人的精神或灵魂。
气血:指人的血液和气息。
凋颓:衰老。
崇:尊敬。
重:重视。
抱朴子:抱朴子是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的别称,他的著作《抱朴子》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道教、炼丹术、医药、养生等方面的内容。
质正:指人的本质纯正,不矫揉造作。
贵行贱言:重视行为,轻视言语,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为政者:指治理国家的人。
不尚文辨:不崇尚文辞辩论,即不重视口头上的争辩。
修道者:指修炼道教的人。
不崇辞说:不崇尚辞藻华丽的言辞。
风俗衰薄:指社会风气衰落,道德沦丧。
外饰弥繁:外表装饰越来越复杂。
方策:指书籍、文献。
儒门:指儒家学派。
术家:指道家、方士等。
初学之徒:指刚开始学习的人。
大要:指重要的道理或核心内容。
干吉:指道教中的仙人。
嵩桂帛:指道教中的仙药。
教诫之言:教导人们修身养性的话语。
大向之指归:指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真诀:指真正的秘籍或诀窍。
口传:口头传授。
寻尺之素:几尺长的白绢,比喻简短的内容。
领带之中:比喻心中。
累勤历试:经过多次的辛勤努力和考验。
杂猥弟子:指杂乱无章的弟子。
用心之疏密:指用心的程度。
履苦之久远:指经受痛苦的持久和深远。
聪明之所逮:指智慧所能达到的。
志力之所能辨:指意志和力量所能分辨的。
囊枕之中:比喻随身携带。
肘腋之下:比喻身边。
秘要之旨:指秘密的精髓。
合药:配制药物。
成分:成分,指药物中的有效成分。
不死:指长生不老。
祠醮:指祭祀和斋醮。
大药:指具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功效的药物。
三牲酒餚:指牛、羊、猪等牲畜和酒食。
延年:延长寿命。
匹夫:指平民百姓。
德之不备:道德不完善。
体之不养:身体不保养。
祝愿鬼神:向鬼神祈求。
不要之书:没有用处的书籍。
举门扣头:跪拜请求。
空坐:空无一物的地方。
烹宰牺牲:宰杀牲畜作为祭品。
烧香请福:烧香祈求福佑。
金丹:道教中的一种炼制长生的药物。
太乙五神:道教中的五位神祇。
陈宝八神:道教中的八位神祇。
穀帛:谷物和丝绸。
亿万:极言其多。
惑亦甚矣:非常糊涂。
异药:特殊的药物。
诵讲:阅读和讲解。
要之师:寻找高明的师傅。
神仙长生度世:成为神仙,长生不老。
空耕石田:在石头地上耕种,比喻徒劳无功。
千仓之收:极言收获的丰富。
適楚而道燕:比喻方向错了。
马虽良而不到:即使马儿再好,也到不了目的地。
校练:检验。
揣测:推测。
博涉素狭:涉猎广泛但基础薄弱。
赏物:欣赏事物。
自誉之子:自夸的人。
秘书:秘籍。
守事之:侍奉他。
外讬有道之名:假托有道的名义。
名过其实:名声超过实际能力。
夸诳:夸大其词,欺骗。
贪浊:贪婪而污浊。
有所请为:有所请求。
强喑呜:强硬地拒绝。
俛仰抑扬:态度傲慢,变化无常。
宝秘:宝贵的秘籍。
深而不可得之状:深奥而难以得到的样子。
礼币:礼物和货币。
执奴仆之役:做奴仆的仆役。
负重涉远:背负重物走远路。
经险履危:经历危险和困难。
积劳自效:通过劳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服苦求哀:忍受苦难,请求同情。
异闻:奇异的消息。
虚引岁月:虚度光阴。
二亲:父母。
捐妻子而不恤:抛弃妻子和孩子而不顾。
戴霜蹈冰:在寒冷中行走。
连年随之:连续多年跟随。
妨资弃力:浪费资财和力气。
卒无所成:最终一无所成。
高名:高贵的名声。
已三四百岁:已经三四百岁。
易名字:改名字。
诈称圣人:假装自己是圣人。
托於人閒:在人前炫耀。
承事之者:侍奉他的人。
不喜书其人之姓名:不喜欢写下这些人的名字。
俗閒:世俗之间。
妍蚩:美丑。
共吹扬:共同吹捧。
妖妄:荒诞不经。
虚生华誉:虚假地产生名誉。
歙习遂广:逐渐传播开来。
莫能甄别:无法辨别。
偶不留意澄察:偶尔不留意观察。
任两耳:只听信别人的话。
误於学者:误导了学者。
规势利者:谋求权势和利益的人。
迟速皆受殃罚:无论早晚都会受到惩罚。
天网:天意,指自然法则。
漏:遗漏。
误有志者可念耳:误导有志向的人,令人深思。
逐空声:追逐虚名。
鲜能校实:很少能够辨别真伪。
甲乙多弟子:有众多弟子的师傅。
载驰竞逐:急忙追赶。
为相聚守之徒:成为追随的人。
崇重:尊重。
愚陋之人:愚昧无知的人。
精:精细,指深入研究和辨别。
仞之垄:极高的山丘。
干天之木:能够触及天空的树木。
漉牛迹之中:在牛的脚印中。
索吞舟之鳞:寻找能够吞舟的鱼鳞。
安能得乎:怎么可能得到呢?
求师为务:寻求师傅作为主要任务。
详择:仔细选择。
陋狭之夫:见识短浅的人。
行浅德薄:行为浅薄,道德薄弱。
功微缘少:功绩微小,缘分少。
成人之道: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道路。
功课:修行。
塞人重恩:满足人们对恩惠的期望。
深思其趣:深入思考其中的趣味。
勿令徒劳:不要白白浪费精力。
虚名之道士:指那些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道术的道士。
诳诈:欺骗,欺诈。
护短匿愚:保护自己的短处,隐藏自己的愚昧无知。
耻於不知:因为不知道而感到羞耻。
阳若以博涉已足:表面上好像已经足够博学。
行求请问於胜己者:向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请教。
蠢尔守穷:愚蠢地固守自己的贫穷。
面墙而立:面对墙壁站立,比喻无所作为。
拱默:保持沉默。
憎忌於实有道者:嫉妒那些真正有道德的人。
谤毁之:诽谤和诋毁他们。
声名之过己:名声超过了自己。
合致弟子:吸引弟子。
财力:财富。
情欲:情感和欲望。
天高听卑:天虽然高,但能听到低处。
斯殃:这样的灾祸。
贫者:贫穷的人。
妄云:胡说。
贱者:地位低下的人。
虚云:虚假地说。
道德:道德品质。
门生弟子:学生。
俗人:普通人。
妒善之心:嫉妒善良的心。
忠信快意:忠诚、诚信、快乐。
亻敝然:心胸狭窄的样子。
神明:神灵。
纱幌:窗帘。
轩房:房屋。
倨慢:傲慢。
窃锺枨物:偷钟声和木器。
铿然有声:发出响亮的声音。
聋瞽:瞎子和聋子,比喻愚昧无知。
华名:好名声。
声价:名声和地位。
患疾胜己:嫉妒比自己强的人。
唇吻为刃锋:用言语作为刀剑。
毁誉为朋党:用诽谤和赞誉作为党派。
貌合行离:表面上和睦,实际上分离。
阳敦同志之言:表面上诚恳地谈论同志之情。
阴挟蜂虿之毒:暗中怀着像蜂虿一样的毒性。
符檄:文书,这里指招致灾祸的标志。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缉熙:光明照耀,比喻学问的进步。
射御:射箭和骑马,古代的武艺。
书数:书写和计算,指文化知识。
农桑:农业和蚕桑,指农业劳动。
规矩:规则和法度。
师授:老师的传授。
救恤死事:拯救死亡的事情,这里指延年益寿。
笃暗:愚昧无知。
形影:身体和影子,比喻自己。
金丹大法:指最高深的炼丹术。
绝穀:断食。
役使鬼神:驱使鬼神。
坐在立亡:坐着就死去。
瞻视千里:远观千里。
知人盛衰:知道人的兴衰。
发沈祟於幽翳:在阴暗处发现疾病。
知祸福於未萌: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祸福。
杂猥道士:杂乱无章的道士。
起死之效:使死者复生的效果。
耻行请求:以请求为耻。
事先达:事先达到目的。
惜一日之屈:珍惜一天的不屈。
甘罔极之痛:愿意忍受极大的痛苦。
不见事类:不懂得事情的本质。
死王乐为生鼠:宁愿做死去的国王也不愿做活着的老鼠,比喻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失去地位。
治国而国平:治理国家而国家太平。
治身而身生:修养自身而身体安康。
玄妙:深奥微妙。
黍稷:谷物,这里比喻可以学习得到的东西。
播种得:播种就能收获。
嘉禾:好禾,比喻好的结果。
泰始明昌国文-古籍-抱朴子-内篇-勤求-评注
抱朴子在这段文字中,首先批判了那些虚名道士的行为。他指出这些道士善于欺诈,以欺骗学者为乐,同时他们又护短藏愚,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表面上看似博学,实际上却不愿向比自己更有道的人请教,固守己见,如同面对墙壁而立。这种态度并非出于对长生之道的追求,而是为了吸引弟子,图谋他们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欲望。抱朴子认为,这些道士最终会受到天意的惩罚,因为天高听卑,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报应。
抱朴子进一步指出,无论是贫穷还是低贱,都不应该虚张声势,更不用说道德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了。他强调,道士应该以忠信和快意为生,而不是心怀嫉妒。他批评那些自以为是、掩耳盗铃的人,认为他们如同聋盲之人,只想要独占名声和徒众,追求外在的名声和内在的财富,这种心态比俗人争权夺势还要严重。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抱朴子提到,即使是学习五经,也应该不耻下问,不断进步。至于射箭、骑马、书法、算数、农桑、规矩等技艺,都需要师傅的指导才能精通。学习长生之道也是如此,想要延年益寿,就必须像救死扶伤一样认真对待。他批评那些不愿请教、固守无知的人,认为这是愚蠢的表现。
抱朴子认为,即使是面对死罪,如果有人能够救之,也会毫不犹豫地付出努力。然而,那些杂乱的道士却因为得不到金丹大法,无法长生,却仍然羞于请求,不愿向有成就的人学习。他认为,这种心态是不明智的,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人,都无法用金钱或权力来衡量。
抱朴子还提到,古代的道书大多追求华丽的言辞,而忽略了长生之道的实质。他希望迷途的人能够回头,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忠告。他强调,人都有过错,但只要能够改正,就像日蚀一样,可以恢复光明。他希望后来的修道者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道路。
最后,抱朴子强调,学习道术和养生之道,必须选择正确的师傅。如果跟错了人,不仅自己无法成就,还会误导后来者。他相信,长生之道是可以学到的,就像播种黍稷一样,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收获。